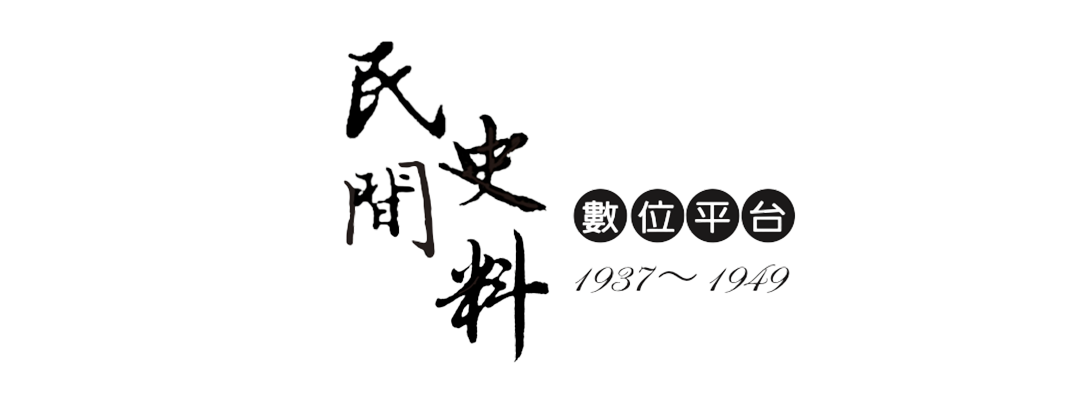更多閻沁恆先生的故事,可以按此。
文/閻沁恆口述、汪琪整理 圖:蘇香霖繪
1937年抗戰爆發的時候我七歲,幾乎由那時候開始一直到高中,我的求學歷程可以說是在不斷的長途跋涉中──避難、逃離、回歸、和再逃離──完成的。
我們家在抗戰爆發前是家鄉的大地主;一個村子裡如果有五、六十戶人家,地主只有一兩家。我的父親是高級師範學院畢業的,沒有作過教師、卻從政當了縣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家鄉時而是共產黨勢力範圍、時而是日軍的勢力範圍,卻都找他當縣長,父親只好遠走鄉寧縣、投效閻錫山部隊,由文人轉而從軍。
我有兩個母親,生母和娘(編按:即二媽)。在我們父親的年代,凡是鄉下出來的人,讀了書作了正式公務員或教師,都會再娶一個沒有纏小腳的女子;鄉下的原配也認命,我的母親就是原配。她生了五個孩子,最後只有我一個人留下來。我和生母離別後,就沒有再見過她了。但那個時代的婦女和現在不一樣,現代男女平等,以前,像我母親,我父親要做什麼,她都認命,什麼意見都沒有。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為躲避日軍威脅,許多家長都將小孩送到日本人不會去的偏遠地方讀書。我的家鄉在山西和陝西交界的吉縣,也不很安全,所以小學二年級就被迫離家,到陝西省宜川縣,就讀一所由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辦的兒童保育院(等於小學)。這個系統的學校和山西省政府辦的兒童教養所學校一樣,都是完全公費的住宿學校,學生有來自一般家庭的、但大部分是軍人、公務員和教師的子女。
學校所在的宜川縣離老家約有一、兩百華里。因為路途遙遠,所以一年只有暑假會回家,平日──包括過年,都是在學校度過的。回家時,一開始還有人來接,待年紀稍長,就靠自己走,光單程就要走四、五天;騎騾子、驢子都是有錢人家子女的專利。
民國30年,我11歲的時候,老家已經完全落入共產黨人手中。那年代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沒有規矩、沒有法律,哪一派有勢力就由哪一派主宰。我們那邊本來是國民政府天下,後來變成共產黨天下。日本人偶爾來,燒殺之餘拿著刺刀向村民搜刮雞鴨作物。日本人來,八路就跑了,日本人走了,八路又來了。我們家因為是當地的大地主,而地主正是共產黨要鬥爭的對象,所以我要是留下來,一定會被迫害。那時候幾個兄弟姊妹,只剩我一人還在老家,因此父親命我去閻錫山部隊駐守的隰縣去找他。後來大陸淪陷時,我母親和嬸嬸留了下來,結果她們被當成驢、牛、馬使喚;北方人吃麵食,她們每天就得去拖石磨、磨麵。
離開母親、投靠父親
母親一字不識,但很懂得小孩子在鄉下不能讀書、又被共產黨迫害,將來一定沒有前途,她就毫不考慮堅持要送我走。由於從老家到父親的所在地必須先由共產黨的佔領區經過日本佔領區、再由日軍佔領區進入國軍佔領區,因此出發前必須先去共產黨指派的村長處拿路條,上面寫了姓名、年齡、目的地等等。由於我們家正好在一條路的路口,一出門就會看到衛兵,因此衣裝打扮絕不能給人要遠行的感覺,更不能帶著大件行李;身上帶的只有一個手拎的小布包,裡面裝著路條、證件和一點錢。除了裝扮,母親特別叮囑: 被盤查時態度要儘量自然,不能被看出有隱瞞,衛兵若問為何出門,就答說幾十里外的親戚有事,要去探望。
出發的那天,天不亮母親就帶我上路,碰到崗哨的衛兵盤查,有問有答,他們看不出有什麼破綻,就放行了。母子兩人走了二十華里,在另一個村子和一位堂姐會合,之後母親自己回家,堂姐和我開始長途跋涉。
堂姐是三叔的女兒。我父親是老大,弟兄三個,三叔早年肺病過世,堂姐把我們家當成她自己的家,和我們感情很深。當時堂姐也不過十六、七歲,但因為父母親都不在了,她很懂事、也很能幹。堂姐本來已經離開家鄉,為了帶我去找父親,她特地又回到家鄉。
由老家到隰縣,沿途處處都是成群結隊逃難的百姓;除山西人還有不少河南人,因為河南除了戰火還有水患,不走不行。或許因為大家都離鄉背井,心態上反而比較寬厚,偷、搶或欺凌弱小的事情很少聽說。而我因為在家鄉已經見識過日本軍人動不動刺刀相向,冒險出走並不覺得害怕。
幸好我們運氣不錯,沿途沒有被崗哨扣留,只是一路都要靠兩隻腳走,孩子也不例外。那年代我們沒有皮鞋,甚至根本也沒有鞋可以買,腳上的布鞋都是家裡自己做的,鞋底用蔴繩加強耐磨度,如果好好的用,正常可以支持我們走上兩、三個月的路。至於飲食,沿路可以買到一些簡單的食物,例如雞蛋、玉米,口渴了,就取河水、井水來喝,如此一走二、三十華里,不是問題。夜晚住宿,則靠親戚接應,其中一站是外公外婆家所在的介休縣,就在山西有名的平繇古城旁邊。
到了日本佔領區
輾轉幾天,堂姐把我帶到沁縣縣城,也是鐵路公路的交通線上,終於上火車到了日本佔領區。那時候抗戰已經進入第二年,日本軍閥以為三個月可以拿下中國,結果陷入泥沼之中,所以十分苦惱。當時有一些中國人的漢奸隊伍替日本人打仗,但日本自己的軍隊不多;哪裡有戰事,就要把軍隊調過去支援,而汪精衛的軍隊不過是象徵性的;他連一支直屬部隊都沒有。所以有時候日本佔領的縣城變成真空,常常只有幾名日本憲兵留守,我們都曉得。
話雖如此,進入日本佔領區,還是得知道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那時正巧老家村子裡一位同鄉,在共產黨、日軍和國民政府三方勢力的交界地區做縣長,是我們進進出出都要經過的地方,有事可以去找他,他就教我們,見到日本人要怎樣行禮,連做什麼動作都有一定;最忌諱的是立正行軍禮,這樣他們會認為你受過軍事訓練,那就完了。
戰時山西沒有郵政服務,所以信都是託熟人帶的。由老家鄉下到日本佔領區,路上行程和辦旅行證件,花了二、三天時間。到了娘那裡,住了三、四個月,一邊找人帶信,聯絡、安排去找父親的旅程;最重要是得弄清楚如何離開日本佔領區、進入政府軍的區域。離開娘,我和堂姐又走了約三十華里,終於到了山西和陝西交界的、閻錫山部隊駐防的地方,找到父親,結束這段避難的旅程。
和父親團圓後,我被安排到當地的兒童保育院繼續就讀。但是後來日本人把閻錫山的部隊趕到胡宗南的佔領地區,山西就全部淪陷了。
遺族學校
民國33年,也是抗戰勝利前一年,父親因公殉職。當時他在閻錫山麾下掌管軍需,也就是負責籌措軍中需要的所有糧食和物資例如棉花等。那時候需要這些物資的不只國軍,還有八路軍和日軍,因此幾乎每一天都承受很大壓力;那時候軍中普遍營養不良,同時缺醫、缺藥,常常連土醫生都沒有,因此一旦得病,往往束手無策。
抗戰勝利,我小學畢業。大家忙著接收、復員,卻把學校、師生丟下、沒人理會。這時師生中比較年長的就認為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回到光復的地區,於是大家帶著學校的物資──包括學校裡的60多枝步槍、子彈(這些平常是不給學生用的)、揹著行李,由老師帶著,踏上了往太原的旅程。一開始一天要走三、四十華里路程,一直到鐵路交通線上的介休縣,才搭到載貨的火車,我們一個個坐在行李上,像逃難一樣,回到了太原。
回到山西太原之後,我轉到閻錫山創辦的、山西最好的晉山中學讀初中,那時候學校的老師,很多是由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清華大學畢業的山西人回鄉擔任教師的,所以這個學校的學生無論到哪裡去,程度都不會比別人差。但是沒有多久,也就是民國37年,山西已經被共產黨包圍得水洩不通。恰巧這時候南京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全國招生,校長是蔣介石,分配給山西有10個名額。那時什麼信息都不通,但有一位我的小學老師在教育廳當秘書,我記得他姓陳,他看到這個消息,竟然想起有姓閻的兩兄弟功課很好,印象非常深刻,就到處找我們。有一天他發現警察局的分局長姓閻,一問果然就是我叔叔。
遺族學校本來有七、八百人,我進去讀高中一年級,是最高班。徐蚌會戰之後學校開始撤退,一路從南京退到杭州、到江西、再到廣東。遺族學校因為學生際遇比較特殊,所以無論哪個省分,負責人看到我們都特別照顧。我們在撤退的過程當中,有很多人沿路回到自己的家鄉,我們兄弟的家鄉太遠回不去,只好跟著學校一路撤退到廣州。在廣州住了半年,戰局惡化、廣州守不住,就來了台灣。
當時遺族學校學生來到台灣的,有四百六十多人。到台灣之後,學校就解散了,學生被分配到各個中學就讀。民國39年,蔣夫人到師大實驗附中召見我們,告訴我們國家有嚴重危難,我們不能和一般青年子弟一樣,讀高中讀大學,要繼承父親的遺志,要提早報效國家。我同學中體格最好的於是從軍了;空軍、海軍都有,體格比較差的讀其他軍事學校,更差的就到職業學校。從軍的那批同學,軍階最高的作到少將,還有最早打下米格機的空軍飛官。我卻剛好因為重病,幾乎命都沒保住,所以他們就沒有找我。
數十年後的今天回想從前,感覺人生的際遇真是很奇特;當年許多年輕人在兵荒馬亂之中喪了命,而我每一關都過了;又設想那時候如果我不想離開母親、或是老師看到遺族學校招生沒有想起我、或是想起我但沒有找到我,或是遺族學校學生被分發軍校的時候我沒有生病,我的命運都會完完全全地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