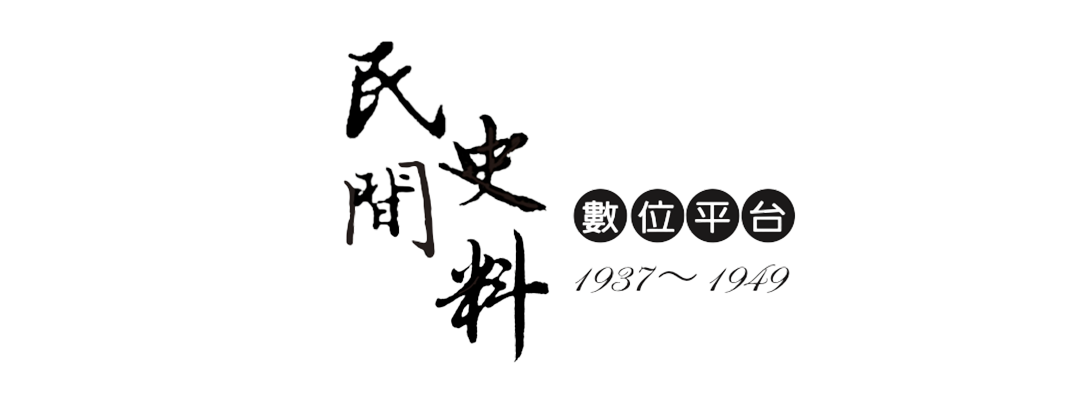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編按】
林彩美出身於日據殖民時期苗栗通霄的小商人家庭,卻成為當地第一個考上彰化女中的學生,爾後進入當時也不容易考上的台灣省立農學院。在台灣省立農學院,她遇到了戴國煇。畢業後,為了追求愛情,也為了呼吸自由的空氣,林彩美毅然單程機票遠赴日本。結婚後進入東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然而,在修完所有博士學分後,她選擇放棄撰寫博士論文,專心投入家庭。
生長在台灣殖民時代的她,經歷過戰爭、1950年代滯悶的台灣環境,以及戰後東京的重建,從傲骨不肯認輸的女學生,到專心奉獻家庭、以襄助夫婿事業為己志的賢妻良母,她是一個走過二戰時代的女子,她的故事顯現那個年代女子的選擇,其中有勇氣、毅力,也有轉身放棄的決然,她將身邊巧遇的機緣,無論幸與不幸,都書寫成一幅美麗的人生篇章。
至於林彩美女士的夫婿戴國煇教授,是公認台灣史研究的先驅。他在1970年代首開研究台灣史先河, 1989年出版《台灣總體相》, 1994年出版《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前者揭櫫台灣史研究須建構主體性,後者以心理學的依附理論,來談台灣與中國大陸互利共生的關係。戴教授晚年的作品:《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總結他一生致力探索「從殖民地的孩子,到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的台灣史觀點,也可隱微看出曾被前總統李登輝延攬回台、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他,對兩岸政策觀點的不同。戴教授1996年回台,2001年過世,但他傳世的台灣史觀點,其影響歷久不衰。
文/林彩美口述 郭以涵、陳淑美訪問整理
圖/林彩美提供
我出生於昭和八年(民國22年)的新竹州苗栗郡通霄庄,土名通霄1。家裡在做小本生意,我媽媽賣水果、餅乾和甘仔糖。這門生意早期是由我阿公開始的,他去山裡有種水果的地方撿選水果,再挑回來讓我媽媽賣。糖果、餅乾也是從外面批發回來的。

我的阿公本是客家人,是個孤兒。被招贅至我阿嬤的閩南人家去後,阿嬤生了幾個男孩,但最後都因為流感瘟疫夭折了。膝下只有三個女兒的他們,決定再替女兒招贅。
我爸爸是我們住家斜對面雜貨店的店員,他家在苑裡的山腳(地名),起初他是因為工作的緣故,才來通霄當店員。當初應該是我阿公阿嬤覺得他看起來乖乖的,才把他招進我們家來。可是我從來都不記得我爸爸,因為後來他就被「離」掉(被離婚)了。從我有記憶起,就是和媽媽、繼父,以及三個弟弟在一起生活2。
我的童年雖然在日本殖民時期中渡過,但我小時候其實很少和日本家庭的孩子來往──除了我家對面的鄰居。
我家對面住著一位台灣醫生,叫作湯長森3。湯醫師本來是別的家庭雙胞胎中的一個,被過繼給湯家的某一房。湯醫生原來過繼的那房人家有另一位小女孩,長大後湯醫師跟那位女孩談起戀愛,最後也步入婚姻。因當時留日比較容易考上醫科,台灣那時候只有台灣大學才有醫科,競爭比較激烈,所以婚後湯先生去日本學醫。不料他去日本後,交到一位學牙科的日本女友,後來也隨著湯醫生返台。
日據時期的日本人在台灣很有勢力,湯先生的女友倚仗著自己的身份,不願意當小老婆。她強烈要求湯先生和他的原配離婚,而當時湯醫師和原配其實已經有一兒一女了,最後好好的一個家庭還是被拆散掉了。湯先生和日本女子育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就成了我兒時的玩伴,我們都叫他們小山內(おさない)桑,因為他們都隨日本太太姓、也取日本名字,沒有姓湯。
湯家房舍前面是醫院,裏頭才是住宅。如果我們生病了,就會去他們家看病、拿藥。平常我都和他們家的孩子在街上玩,很奇怪的是,就是湯家的小孩子從來都不會玩得很髒,也不會邀請我們去他們家玩。大概是覺得我們台灣小孩很髒,也沒鞋子穿吧。
我先上通霄公學校附設的幼稚園,在我七歲的時候,進入了通霄公學校,開始唸書。
當時日本人唸的是小學校,閩南人唸的是公學校。我們平常是都是赤腳,上學也是,唯有一些重要典禮或節日,比如天皇生日或是新曆新年,才穿木屐。所以穿著很好的小學校學生,看到我們都笑我們是雞(にわとり),因為雞沒有穿鞋子。
我是二月生的,當時日本人把開學日訂在四月一號,四月以前生的小孩,日文叫做「早生まれ」(出生於一月到四月的小孩),可以提早入學。因此我剛滿七歲就上學了,不像我的先生戴國煇,他4月15號生,滿八歲才入學。
日人召集漢詩集會
我在公學校裡,從來都沒有被日本老師教過,我都剛好碰上女老師。她們都是台灣人(閩南人,客家人,熟蕃 -比較漢化的原住民),從新竹女中或者台北第三高女畢業的,不會任意兇我們,也不會欺負台灣同胞。如果你是男生4,又剛好碰上日本老師,就可能會遇上罰站,或是頭頂水桶之類的懲罰。運氣不好的時候,還會被打嘴巴。
那時候老師們都兼上很多科,除了日文,還有數學課、修身課5、體育課、圖畫課和音樂課,而裁縫課則是到了五、六年級才會上。當時學校並沒有上英文課和漢學課,漢學私塾我也上過,是學校之外另外學的,用閩南話教。那個時候的日本人,為了表示他們很有文化,殖民地時代剛開始時,男人如果要表示他有學問,就用日文唸漢字,作詩也用漢字。日本人還去召集我們的漢詩人、有學問的人去聚會,一起吟詩、作漢詩。
我上小學的時候,皇民化運動開始了。除了學校會帶我們去虎頭山上的通霄神社參拜,以及升旗時必唱國歌〈君が代〉(きみがよ)外,每天早上街頭也會播體操廣播,大家聽到了,就會去通霄庄街上做radio体操(日文,中文為體操)(たいそう)。雖然這並非強制性的,但大家都很踴躍。我們也不只在街上做,去學校升旗後,也還要做一遍。
感受到戰爭
那時候儘管我年紀還小,仍然能夠感受到戰爭。一方面是因為時不時發生的空襲警報與消防訓練,當時我們家家戶戶都被要求要造防空洞和準備沙包與水。一旦警報響起,我們就躲在自造的防空洞,或是街上公造的,再則就是跑去菜園裡的防空洞,但菜園防空洞其實很簡陋,只是簡單挖一個一家人可以坐進去的空間,上面擺木板和布袋與土。倘若真的有炸彈炸下來,躲進去的人還是會受傷。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家裡可支配的物資一天天匱乏了起來。比如米、糖、肉、布等。比方肉,一個禮拜只配幾兩,都給老人吃。後來也沒有配糖,儘管台灣有種甘蔗產糖,但都被日本殖民政府買起來,給在台的日本人享用,或是送回日本或戰爭前線。我本來天天吃番薯籤飯(那原是豬的食物),後來糧食不夠,米配給也變少,餐餐就變成了番薯籤稀飯,配著無油的水煮青菜,特別難吃。好在通霄靠海,有人會去抓魚,我們可以買到一點點魚,政府再要伸手也很難管。
另外一個政府難管的地方是雞蛋。當時大家都養雞,但因為雞蛋容易壞掉,所以不納入管制範圍。不像我們家養的豬,養大後都不能自己宰殺,只能賣掉,因為私宰犯法,抓到後可能會罰錢或被關。
戰爭來到後期,萬事萬物都成了配給,有錢也買不到任何東西。此外更明顯的,是空襲慢慢變得嚴重起來。大概我九、十歲時,我們還「疏開」(そかい,疏散)6到我們佃農的家,大概離通霄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的路程。我們全家去一個佃農家,我阿姨也是招贅,他們去另外一個佃農家。我們有佃農家可以去是因為我阿公當初靠挑水果、當長工賺錢後,我阿媽節儉地存下來置產,我們家才從佃農變成了小地主,不過後來遇到國民黨政府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又被打回成原形了。
我在小學畢業後,本來應該要報考新竹女中,因為按照規定,我不能跨州就學,因此新竹女中作為新竹唯一的州立女中,就成了我的第一選擇。班老師替我寄了内申書(ないしんしょ,申請書。美軍飛機的空襲之故火車幾乎停駛,爲了安全考生不能到校應考而改用内申書形式))給新竹女中, 內容包含了我的個人資料、成績和家庭情況。但因為我們家不是國語之家[国語の家、國語家庭],也沒有改姓名,所以我沒有被錄取。
我的同班同學,她是我幼稚園老師的小孩,成功申請了國語之家後,就把自己的姓氏「徐」改成了「安川」(やすかわ)。她是我們那屆唯一錄取新竹女中的學生。而我最後被分發到了苗栗的家政女學校(かせいじょがっこう)。
當時新竹州(涵蓋桃園、新竹、苗栗,當時通霄庄屬於新竹州苗栗郡),唯一的州立女中就是新竹女中。家政女學校是繼竹女的第二志願,雖然是「女學校」(じょがっこう)只招收女生,但不像台北叫第二高女。
媽媽不急著嫁我
說起來幸運,我小學畢業還能繼續唸書。當時並不是所有女生都能繼續升學;通常女孩小學畢業後就在家幫忙、準備嫁人。但是我媽媽個性比較好強,她並不覺得只有男孩子才可以唸書,只要是她的小孩子能唸書,她就覺得很光榮,並願意給與支持。我應該算是可以讀書的女生吧,因此可以繼續升學。
從我們通霄到苗栗的家政女學校很遠,隔好幾座山。那時候交通工具很缺乏,火車因為戰爭空襲,也不一定準時。我們會想辦法搭火車,有時候也用走的到家政女學校。學校並沒有提供宿舍,家政女學校的學生大概都要在苗栗租屋,上學時再走路去學校,從苗栗到通霄約走2至3小時。剛好我們通霄也有比我高班的人去唸,於是我們就常結伴同行,到苗栗才分手,各自回租屋處。
在我入學幾個月後,某一天美軍轟炸了苗栗的製油所,儘管我們學校離礦區很遠,但那個直入雲霄的大煙把我們都嚇壞了。我趕緊收拾行李,和那些比我高年級的同學們一起回通霄,一路上我們只要聽到飛機聲或是空襲警報,就趴在低窪地裡,或是躲在大樹下。同一天,通霄也遭受美軍的空襲,估計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移動中的火車或貨車,所以連排掃射。當天我們街上的一個小孩也被射到了,而我也藉此機會,再也不去那所我不喜歡的家政女學校了。

不去學校的原因,除了空襲被嚇到,還有家政女學校學生畢竟不如竹女學生有地位。那時家政女學校學生走過苗栗街上,小孩看到我們穿的戰時的「國防服」(戰爭時,學生的打扮:短和服上衣與長褲),都會笑我們「がまエッエッ」(青蛙叫聲),為何會這樣笑我們,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但我討厭被笑,也就不去家政女學校了。
光復之後
沒多久後,我們終於迎來了光復。8月15號當天我們並沒有聽到天皇放送說戰敗,因為我們家沒有收音機。我們小孩子都是從大人們的奔走相告中聽來的,大家訴說的臉龐都散發著喜悅。後來我們聽說受降典禮辦在10月25號,於是還有人自發地舉旗在通霄街上遊行。我當時也跑去參與了,我在隊伍裡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到了晚上則改成提燈籠遊行。
當時,國軍來到通霄後,住在小學教室,等他們搬走要經過一段時間,小學才會回復正常運作。我們滿心雀喜地歡迎他們,結果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支穿著草鞋、衣服破爛,還挑著鍋碗瓢盆的軍隊,我不知道這些是軍伕還是軍人,但只知道日本人向來愛面子,不會給殖民地的人看到不體面的一面,我們之前看到的日本軍人素來穿戴整齊、威風凜凜的,也許國民黨軍隊本來就沒有那麼講究,但當時我們覺得很失落,他們好像乞丐軍。
除了軍人,當時,我們跟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接觸,還有便服警察,跟教本省人國語的外省籍老師,也有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我們稱「半山」,「半山」的穿著好像比我們講究,但不管外省人跟「半山」跟我們都很少接觸,也無所謂好印象或壞印象。
自動退學後,平常時我待在家裡幫忙。有一天我背我二弟在廟口玩,剛好碰見了我六年級的老師鍾才妹。她對我說:「さいびさん(我的日本名字彩美),妳要不要回來補習?」因為光復後,班上有一些同學都回去找老師補習考初中了。於是,我就回家問我媽媽,我說:「才妹老師在問我要不要回到學校去補習?去補習就是要重考初中。」我媽媽說:「好啊!」所以隔了一、兩天,我就直接去了。我們當時就只補國文和數學,因為這兩科是考試科目,我補了一年左右,到可以考試的時候,我報考了彰化女中。
從日文到半吊子國語
在日據時代,日本人都希望我們無論書寫或講話都用日文,在家裡也用日文,但是家裡有長輩,他們平常都說河洛話,根本不會日文,怎麼可能全部用日文。等到國民黨來了之後,要我們學國語,其實那時教我們的台灣老師也剛學會注音符號,所以當時的情況大概是老師昨天學,今天教給我們。
那時候到台灣的外省人好像每個人就順理成章地變成國文老師,可以到學校教我們。很有趣的是,有些私塾的漢學老師也開始教國語,但他們也是半吊子,只是把國字唸成閩南語的音。雖然是這樣,我們也只能接受,慢慢調整。但我很感謝當時幫我補習的老師,她並沒有收我補習費,所以我媽媽都塞一些物資給老師。
我沒有考新竹女中,一來是因為上次它沒有錄取我,我有點賭氣想,「這次換我不要你」,二來是因為去新竹的時候要在竹南換車,我們海線要換成山線,很麻煩,但到彰化就不用,直接走海線即可。
去彰女唸書可以選擇住校,或是每天從通霄坐火車通勤。但是因為坐火車要早上六點上車,我媽媽很忙,沒有把握在早上六點前弄好我的早餐和便當,於是她就讓我去住校了,免得天天提心吊膽來不及。我是通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去彰女唸書的人,當時沒有人和我作伴,所以我一個人帶著一只大的舊皮箱,懷裡揣著學費,自己坐火車去報到。
小白兔原來是小白狼
那個舊皮箱是從床下拉出來的,真的很舊,加上沒有人送我,我一個人笨拙地前行。我從彰化車站出來的時候,被一群男生看到,其中一個用著開玩笑地語氣說:「欸你看,那個人!那個拿著很舊的皮箱的,就是我妹妹。」有點故意嘲笑我很土氣的味道,我不曉得他妹妹當時有沒有在那裡,他比手畫腳地指著我,大概是因為我是在場最顯眼的一個。其實我也不想帶那個舊皮箱,可是沒有辦法,家裡沒東西可以裝。後來我才知道他妹妹也跟我同班,他們是從大甲來的。大甲比通霄還大,還繁榮一點,而且她家好像也是做生意,但不是像我媽媽做的那種小生意。
我到學校後,就開始找宿舍。我很客氣地問了一個經過的女生:「能不能告訴我宿舍在哪裡?」,但是看到我那麼土,還拖一個大皮箱,她「哼!」了一聲,扭頭就走了。我當時心想,「好,我會把妳記得的」。後來我發現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也來自彰化,之前讀的是離我們學校不遠的民生小學。民生小學只收女生,再加上地利之便,所以我們班一半以上都來自民生小學。我進教室的時候,她們湊成一堆、一堆地在閒聊,感覺好像只有我一個從鄉下來的。當時我就下決心:「我才不會輸妳們!」我那時「刺牙牙」(河洛話:比喻很好強。為了保護自己,就表現得像刺蝟一樣),只想贏過她們。連體育課的「跳箱」,我都跳了四、五層,每次跳箱我都一次就跳過,迎來同學們一片驚嘆。
後來我跟那個不理我的同學說:「我那個時候問妳宿舍在哪裡,妳還『哼!』這樣。」她回我:「拍謝啦!」我那時穿著很土,又拉個舊皮箱,剛進彰化女中時,真的很像誤闖叢林的小白兔,不服氣的我當時只想把小白兔變成小白狼。
在彰女的時候,我們一個禮拜上六天課,周末才回家。平常時都在學校搭伙食,我們不用繳餐費,而是繳米,周末返家我們都會順便抱米回學校,大約是一人一個月的飯量,多少斤忘記了。繳米是因為當時物價波動得很厲害,學校才會有「現物制度」(繳實際物品的制度),而米算是大宗商品,具有指標性,所以被拿來交易。每個人每個月都要交一定份量,不管你吃多、吃少。學校裡也有職員會秤米和記帳,一旦每月該帶的米夠足了,就不用再繳了。
當時三餐的白飯也是學校分配好的,有時我吃完還想要添,也不敢,因為高年級會盯著我們。那時候我們遇到高年級的,都要用日文叫:「姐姐(お姉さん、お姉さま)」。比我們高一個年級,就叫她的名字,後面加上「姉さん」;高我們兩個年級以上,則是名字加「お姉さん」,高三年級則再加上「お姉さま」,一級比一級尊敬之意。儘管已經光復了,可是我們和高年級的都受過日據時代的教育,所以相處間還會有用敬稱的習俗。
抓共產黨草木皆兵
後來宿舍有認妹妹、認姐姐的習俗,因此比我低年級的都叫我「彩美姊姊」,不過我們不像以前有很多的階級,只是我們作為姊姊的,要稍微照顧一下妹妹,教她各種宿舍和學校的事。
我在彰女一直維持甲班的成績。在讀完初中後,順利地直升上了高中。在我高二、高三的時候,蔣介石加強抓捕共產黨的力道,因為當時共產黨確實有解放台灣的意向,他們可能會藉著蔣軍撤退的時候,或是以探親、作生意的名義潛入。蔣介石丟掉大陸、退到台灣後,就膽戰心驚、草木皆兵,因此那時候社會上還流傳著一種說法,抓一百個裡頭,只要有一個是真的,他們就值得了,所以說當時白色恐怖時代亂抓得很多。
像在彰化女中,我們那些來自大陸的老師,很多都是從基隆、台北一路逃過來的,比如我們的國文老師羅卓才,就是有人在台北車站附近看到佈告的槍斃名單上有他的名字,他應該聽到風聲才往南逃。他在彰女沒多久,又匆匆逃了,後來聘請他的皇甫珪校長沒多久,也被換掉。我們的師長換了又換,再加上我們住校的不能去補習,以至於我們的課程學習很多部分都連接不上,零零落落的。
那時候在彰化女中有上英文課、國文課、數學課、體育課、音樂課、家政課,還有要學三民主義的公民課。此外,學校也有教生物、物理和化學,偶爾也會做一些簡單的實驗。我那時候數學最差,考大學時就不敢考理科。選科系時也只能隨意選,最後沒有考上台大,就上了台灣省立農學院(也就是現在的中興大學)的農經系。當時大學就只有台大、師大、台灣省立農學院(現在的中興大學)、台灣省立工學院(現在的成大)等幾所大學,當時的台灣省立農學院還沒有文學、商學院等其他學院,但也是跟大學同級的「大專院校」,都是獨立招生。
注解
11935年(昭和10年)4月21日早上六點發生了新竹到台中的大地震,芮氏規模為7.1,俗稱「大地動」。當時我在前院的地方爬,旁邊有剛煮好的稀飯在冷卻,我本來就爬不穩了,再加上地震的晃動,我直接跌入稀飯中,右手肘關節處大面積燙傷,此後餘生都一直帶著燒傷的印記。
2自從我會爬後,因為母親忙於生意,所以她有時就用背帶把我綁在榕樹下,讓我在地上任意爬行玩耍。我總是弄得滿身塵土,有時還會不慎跌落乾涸的水溝裡。待我長大、離家就讀於彰化女中時,某天我返家遇上了同庄愛開玩笑的鄰居阿伯,他看我亭亭玉立,一改過去的土氣時,還用河洛話笑我說:「你還記得你以前都在地上抓雞屎吃嗎?」因此我現在90歲了,別人問我身體健朗的秘訣,我都跟別人說:「因為我是吃雞屎長大的」。所以經歷過貧窮時代的林彩美,常笑自己是被淘汰剩下的碩果,因此百毒不侵,直至現在身體仍健朗。
3湯長森,生於清光緒26年(1900年)。父親湯祿曾任通霄庄庄長達26年之久,兄弟四人,台灣光復後,先後擔任通霄接管委員。湯長森畢業於通霄公學校、台北國語學校國語科(即今之國立台北師範大學)、日本慈惠醫科大學耳鼻喉科。畢業後,擔任日本警視廳(相當於我國之警政署)之専科醫師三年半。29歲時返回通霄庄,開業於慈惠宫旁,民國79年以高齡91歲去世,行醫先後達62年之久。(道卡斯文史工作室)
4通霄公學校主要採男女分班,但因為人數通常不是整數,所以有一班是男、女混班。
5「修身」課就是教你怎麼守規矩、守道德等,類似過去國府時期的「公民與道德」課。
6「疏開」是去了就不太回家,基本上是在那裡長居,除非要拿東西才會回家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