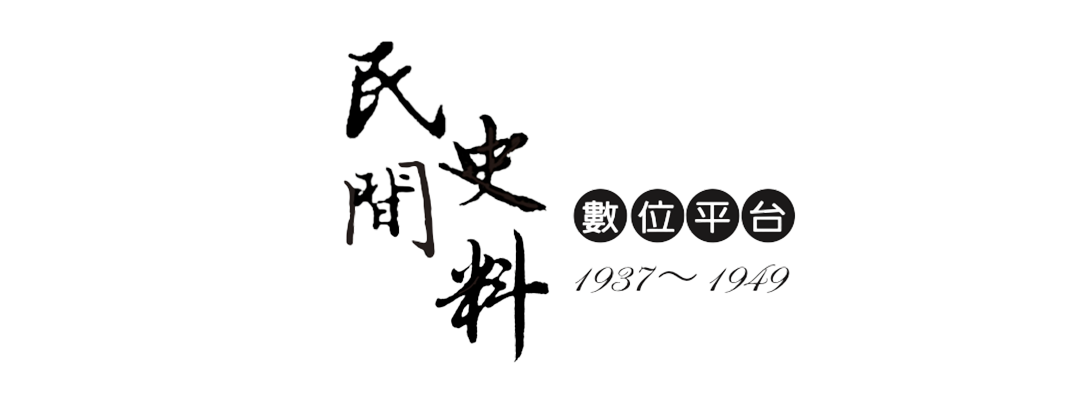文/蘇定遠口述,孫曼蘋、許永耀、汪琪整理¹
圖/蘇定遠提供
我原名蘇文思,1928年9月6日出生於四川成都井研。曾祖父曾經在四川成都考取科甲,並在廣東潮州當官,於辛亥革命逝世,祖父蘇漢卿之後帶著父親和三叔返回四川居住。
父親蘇柱勛,曾先後任井研縣和溫江縣郵政局長,母親賴惠娟出生於書香世家,家中共有十一名兄弟姊妹,可惜有五人夭折。我小學就讀成都市實驗小學,畢業後入讀成都華陽中學。由於抗日戰爭的緣故,父親的工作隨時調動,家裡因而不斷遷徙,我也經常轉學,直到1944年,我16歲才初中畢業。
1944年,蔣介石委員長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萬軍」的口號,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並將這支部隊定名為「青年遠征軍」。我從小就崇拜一些盡忠報國的英雄,如班超、文天祥、岳飛等,決定響應號召從軍報國,父親也支持我去參軍,並將我的名字由蘇文思改成蘇定遠,鼓勵我仿效東漢時的班超投筆從戎,當馬革裹屍還。
1944年秋初,我的體檢及格,獲准入伍。我們這些沒有受過訓的老百姓,連槍都打不來,很快被送到學生軍,通過考試,我被分發到新一軍孫立人部隊學生軍第三隊,有些文化程度較高一點的,就被分到第四隊,接受基本軍事知識和動作訓練,一週後接到通知要派去緬甸。
我們由成都市華洋中心出發,行軍到新津機場趕赴前線。新津機場是美國人幫我們擴建的一個很大的軍用機場。我們經過成都市區時,家家戶戶放鞭炮替我們送行。在城裡大家走得還整齊,一出城隊伍就亂了。我從沒走過夜路,那天從九點多十點,走了整夜約30里山路,我們當中一些年紀輕的,走到都睡著了,有人想了一個辦法,就是用白毛巾把每個人的手連起來,這樣前面帶頭的一動,後面的就醒了。第二天十點鐘到新津機場的時候,大家都很疲勞。
那時的飛機不像現在一般客機有椅子,而是運輸機,坐在機艙兩邊的長凳子上。當時我們沒穿厚重的衣物,飛機升空後氣溫驟然降低、空氣也很稀薄,大家只有擠在一起取暖,一直等到氧氣瓶放開了,我們才感覺舒服了。
那時候滇緬公路被日本人封鎖,飛機要避開日軍的高射砲,必須往喜馬拉雅山區、穿越諸多岔峰飛行。美國的十四航空隊曾經幫我們訓練了很多飛行員,但也被日本高射砲打了很多下來。
飛了約一個多鐘頭後,我們到了相對安全的、靠近印緬交界的一個地方汀江。下機後,我們被告知把衣服和不重要的東西都燒了,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就把衣服脫光。有人身上生瘡,洗完澡,醫衛人員就用黃色的藥往他們的皮膚上抹,然後發給每個人衣服、背包、軍袋(帆布的很大的袋子),內衣內褲等等一大堆。這時候就有很多部隊來接人,哪裡死人需要補充兵員就去哪裡。
我被分發到新一軍38師防毒排。防毒排的主要任務是用衝鋒槍掩護使用火焰噴射器的士兵。日軍依靠地形和森林,建了不少碉堡、交通坑等防禦工事。火焰噴射器有效射程達30米,每次大部隊進攻前,我們都先用烈火摧毀日軍的防禦工事。
叢林裡的蚊蟲很厲害,咬到可能會傳染上瘧疾(四川人叫「打擺子」),所以我們每天早上排隊拿水壺、領一顆奎寧丸;奎寧丸治瘧疾,每天早上要吃一顆防染病。至於飲水,開水是沒有的,水壺裡裝的就是河水加一些消毒藥,有的同學吃不了苦,意志就會動搖。
我們到緬甸的時候,密支那已經收復了,兩邊死亡人數都是兩萬多、接近三萬,日本也是差不多,這些是我看到的、聽到的、有些是長官來跟我們講的,我就把它記起來了。
密支那收復後,我們從八莫繼續前進,穿越雨林,打了約一個多月,一直打到緬甸的南坎,和兩千多公里長的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後來改稱史迪威公路,以紀念美國的史迪威將軍),戰事十分慘烈。
1945年約三月份,我們回國了;先到廣東、再轉到廣西南寧,那時戰事還沒有蔓延過去。我們的班(一個排四個班)被派駐防廣西貴縣,有些到玉林,但梧州就不能去了,因梧州經常淹水,連房子都淹了、一片汪洋。
在貴縣時,我們部隊和美國通訊部隊的營區靠在一起,有天晚上聽到「嗶嗶波波、嗶嗶波波」的聲音,卡賓槍跟衝鋒槍打得很厲害,排長就派我們同學裡面年紀大一點的出去打聽,結果他們回來說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了,大家高興得不得了,那時我們才出來一年多。
日本投降後,政府派了新六軍接收上海,廣州市就由新一軍接收。因為怕日本人把重要設備毀壞了,所以我們連天連夜趕路。那時交通不方便,要靠民家的大木船來運防毒排的器械,包括防毒器具和裝載氧氣等氣體的瓶子──這些又長又重的瓶子連我們都拿不動的,廣西女人卻很厲害,她們都可以抬。因為木船載重量大,所以臨時找來四位年紀大一點、力氣好一點的同學,加入划船的陣營。
進廣州市的時候,打頭陣的是我們直屬部隊(13團、14團)的兩個班。那時日本還沒有正式投降,日本軍人端起槍,所有老百姓走他們面前過,都得鞠躬敬禮才讓你走。我們到了廣州,起初是駐防在沙河一個學校裡面,後來轉到沙面,一直到九月份。
第二年內戰爆發,我們被派往東北,於是坐廣九火車到香港,連夜在尖沙咀發裝備。裝備分幾種:軍官的、軍人的、一般的,都有品級的。我們從尖沙咀上船後,因為有波浪,船身擺來擺去,裡面掛的東西也隨著擺來擺去,有些同學身體不大好的受不了、起不了床,比較嚴重的,把吃的東西──甚至連黃水──都吐出來。我身體還好,年輕也不懂,有時候還可以到甲板上去看一下。
走了九天九夜後,我們從塘沽登陸。那陣子蘇聯與共產黨合作,本來我們可以從葫蘆島或大連登陸的,但是共產黨動作快,國府派去接收東北工礦的張莘夫副處長(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就被蘇聯派人把他殺了。有人說共產黨的部隊一個月消滅了幾百萬日本關東軍,這不是神話嗎?
後來我被調到司令部留守處人事科當文書,跟著司令部一路從瀋陽去四平街。那時候國共兩邊已經打起來了。北方開始化雪,路很糟,所幸我們的裝備好。有一些穿了老百姓衣服、棉襖,看起來不屬於正規軍人的,就死在鐵路兩邊。當地人看到我們都說:「哎呀國軍你們來了呀,好盼望你們來」,北方人對我們是很有情的。他們說蘇聯夥同那些不是正規軍的部隊會強姦婦女,後來女人出來要把臉塗黑,不然就會遭到強暴。
我們從瀋陽、四平街、到吉林後,又往南走撫順、鞍山,到海城,在海城駐紮得比較久。那時國民黨也是不團結;孫立人和杜聿明的戰略跟戰術不一樣。當時孫立人年輕氣盛、又是留美的,但不管怎麼說,杜聿明都是領導,大家應該商量,但是各搞各的,最後戰事就不順利。
我是1947年第三期退伍的,因為部隊規定,凡自願參軍、學生從軍的,時間到就可以退伍,孫立人說話是非常有信用的。在部隊──尤其是在重要的部隊裡面,如果對打仗有經驗的離開,會對戰鬥力有影響,所以李鴻師長、還有參謀長龍國鈞紛紛挽留,最後學生軍決定分期退伍:1947年三月份第一期、六月份第二期、九月份第三期退伍,我就等到九月份。
那時候要是留下來,還可以保送到長春大學;但我學歷不夠,高中都沒有讀,去唸大學要準備,準備還是不行的話,回到內地還是要讀青年中學,但數、理、化──特別是三角、幾何、代數這些科目是高中才普遍有的,我們哪趕得上?

我們離開部隊後打算回成都,途中路過南京,南京國民政府還懷疑我們,叫我們到差館(派出所),在那邊待了一個月。回到家後,我們當中高中畢業的、或是有高中同等學歷的,都進了四川大學,學歷不夠的,就給了一個消防隊防護團的工作。防護團有些人是義務的,我們才十幾歲,社會上什麼事情都不懂,有事得找人幫忙,但這其實是我的工作,自己都不好意思;加上一個月給一斗米,結了婚的養家都養不起,所以很不得意,最後就離開了。後來又重新投入國軍隊伍,至1949年因病請求離職,最後輾轉到香港投靠親友。
[後記]
1950年,蘇定遠回廣州,透過戰友關係,獲人民政府安排於廣州越秀公安分局工作,一年後因為曾是國軍遭到辭退,被送去開發新疆克拉瑪依油田。在反右等連串政治運動期間,蘇定遠又以曾為國軍的背景,被冠上各種罪名,在新疆烏魯木齊監獄和伊犁農場遭到嚴重傷害,至1963年才獲釋,依靠打散工和體力工作維生。
1981年到香港,在工廠工作至2000年退休。
注解
¹蘇定遠先生的訪談由許永耀於2022年5月22日完成,參考資料包括:袁梅芳、呂牧昀編著,《中國遠征軍》,紅出版(青森文化),2015年;<蘇氏老兵故事>遠征軍老兵蘇定遠:為國家民族我不後悔,每日頭條,2019年10月14日;〈88歲遠征軍老兵憶戰場:手持衝鋒槍,掩護噴火兵〉,華夏經緯網-人人焦點,2020年12月21日;〈香港抗戰老兵蘇定遠〉抗日戰爭紀念網-肖像與手模,2019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