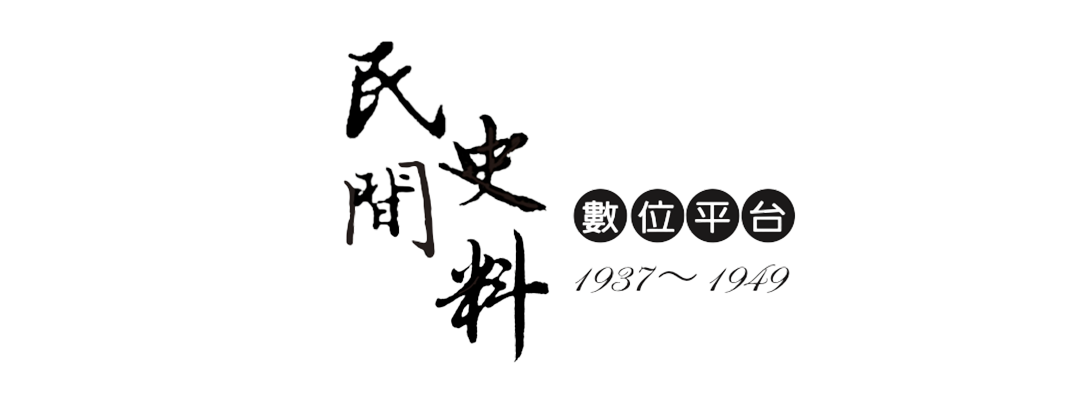本文摘自鈕先銘著《還俗記》,中外圖書出版社於民國六十年出版。

文/鈕先銘,李莉珩編輯
圖/廖文瑋翻拍自南京市之「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
我既然不肯說一句日本話,當然就無法問鬼子為什麼要我們和尚擔柴去?而且是擔到哪裡去?鬼子班長既指定了我,只好再拖那位老農,一同硬着頭皮去了。
鬼子兵先將那些散兵的隊伍押在先頭,五担柴火跟在後面,浩浩蕩蕩的向西走上公路。「他們要我們担到那裏去?」老農輕輕的問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上元門。」我也輕輕的回答,因爲方向是向那邊走。
「他們要柴火幹什麼?」老農還在繼續的問。我還沒有回答,也不知道如何的回答,正在想:眞的他們要柴火幹什麽?是不是要火燒活人。「啪」的一聲,一根木棍子打在我們担的柴上。同時聽到一句怒吼:「Damade」
不知在什麼時候,鬼子班長手裏橫了一根樹枝,來當馬鞭揮着。Damade 在中文寫是「默」字,意思是不准說話。幸好樹枝是打在柴綑上,並沒有打我和老農。
鬼子沿江開槍掃蕩,路面滿是屍體
僅僅才三、二百公尺的路程,沿途却躺了許多死屍,這當然是先前鬼子兵前來永清寺時沿途射殺的。先前由於過份驚恐,鬼子兵從何方而來,我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才知道敵軍是先進了城,然後再從上元門出來,作沿江的掃蕩,根本沒有從燕子磯作沿江十二洞的包圍。所以我和廣東部隊想作礙路的突破,只聽到燕子磯方面的輕機槍聲,而沒有遭受到追擊。我已無法再作重新推測,假設我所率領的廣東部隊不自行散去,是否能够辦到突圍?事已過去,正確抑或是錯誤,已無從倒轉時光來挽回!
可是有一點我得承認,那位自居我副手的廣東軍官,有深度的作戰經驗。當我一個人坐在沿江十二洞公路邊的土溝時,他還回轉頭來拉我,告訴我︰一個人逗留在那裏是極其危險的。
這一點眞不錯,敵軍的掃蕩,一看見可疑的個人必先開槍;而看見一堆可疑的人,反而想包圍起來活拿。前來永清寺的鬼子兵就完全採取這個方式,凡是在樹林間或公路旁的散兵都被射殺,而反而將在永清寺的一大堆人加以保留。我若一個人留在公路旁的土溝邊,當然也不會逃此命運。
當我一走進上元門,我居高臨下的看過去,成千成萬的中國散兵,分成一堆的坐在地下。人數多得驚人,超出了我上午所見到的十倍或百倍。而鬼子兵呢!至多不過是一連或兩連,總不應當在一營以上。
四面都架着輕重機槍,將超過百倍的散兵包圍着。失去了武力,而且哀莫大於心死,一旦甘心做俘虜,人再多也就沒用了。
鬼子兵集結了許多的中國炊事兵在燒飯,整齊的集結了許多的行軍鍋灶在一起,一看就可以明白,這是給俘虜兵吃的。
從永清寺帶來的一羣散兵,到這裏眞是小巫見大巫,到底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一眨眼就沒有看見了,無疑的,在大堆中又增加了一小堆而已。
五擔柴木則被指定送到炊事兵羣去,這倒使我又來一次心驚肉跳。上午我所臨時率領的廣東部隊,就有幾組炊事兵,假設其中有人認出我而叫出一聲,豈不是會令我前功盡棄!我只好在不知不覺間拉低了一下帽子,低着頭解開柴組。
但是我的顧慮是多餘的。每一個被俘的中國兵都是自顧不暇的端坐在人堆裏,一動就遭受到鬼子兵的怒吼,可能槍托就會居高臨下的落在背脊上。一片鴉雀無聲,出聲的只有鬼子兵們,無意義的吼着,或者是用日語叫着,至少他們還沒有找到通譯。這便是被俘後的 羣像。
柴火被交代了之後,四担擔柴的中國兵,當然歸納於俘虜羣。我還有一位老農又如何的辦呢?又緊張起來了,似乎沒有人再來管我們,但又不敢走,眞是進退維谷,哭笑不得!
那知先前的鬼子班長却走了過來,手裏拿了幾筒米——這是像一根粗而長的香腸式的布筒,灰色的,一看便知是中國軍的補給品。他一面遞給我,一面嘴裏叫着:「心焦!心焦!」的發音。
慷他人之慨,將中國軍米送給我們,似乎是沒有問題。只是那一句日本話,我却不懂。以我的日文程度雖不算高,何至於連簡單的單字都聽不懂?眞使我納悶!他看見我還不走,也許他認爲我還不够滿足,又掏出了一包香煙遞給我。這是一包「譽」牌的二十支裝軍用煙,只值日幣七分錢,是日本最廉價的菸,我在日本的部隊中抽過。這是只准日本士兵買的,連士官學校都沒有得賣。因爲日本士官學校是禁煙的,雖然對中國學生並不嚴格,可是並不預備軍用菸供給我們。事隔八、九年,今日以準俘虜的身份,而接到一包日本軍煙,眞使我感慨。
當他將香煙遞給我以後,馬上揮着手。這是快走的意思,我聽懂了,馬上搓着頸上戴的佛珠子,合掌恭敬的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便和那位老農逃出了上元門。在城門口守衛的鬼子也沒有阻攔我們,我向他點了一個頭,揚了一揚手上的那包軍煙,它當作了我的通行證。
老農走出上元門,才鬆了一口氣,他說:「我以爲他們要拉夫呢?」
老農和我所緊張的觀點不同,我所顧慮的是怕被發現身份,怕被叫去虐待俘虜;而老農呢却怕的是被拉夫。拉夫這個名詞,好像在台灣的字典中,業已被刪除了,可是在大陸的舊式部隊中,拉夫簡直是部隊的特權權利。那是因爲許多雜牌部隊,根本不講求供應和補給,所以一到部隊開發,便施行拉夫,以權充人力的補充。老農還是抱着這種舊式的觀念,所以顧慮的只是拉夫。
「我也沒有想到,要我們担柴來,是爲了給我們幾筒米。」我文不對題的答覆老農。「他們爲什麼要給我們米?」他又懷疑的問着。「我也弄不清楚!」
照敵軍那種殘暴行爲來講,不可能有慈悲爲懷的心腸。從嚴格的來說:那怕是一筒軍米,既屬於「戰利品」,也絕不是一位班長可以加以隨便處理;可是這是屬於一種戰場心理的變態,他要虐待我們一次,要我們担柴,然後又施以小惠,以表現他的威武和權力,那怕他僅僅是一個小小的班長。
我們在歸途中已經是夜幕低垂,所幸南面是小丘陵高地,碎石子的黃土公路,在白雲的反射下還勉强的看得清楚。我們就急促想奔回永清寺,幸好已天黑,上元門外,並沒有敵軍巡邏部隊,否則那是極其危險的場合。
「啊呀!」我驚叫着。原來是一個死屍,擋在公路上,幾乎絆我一跤。這不可能是我們進城的這一段短時間所被虐殺的,在我們來的時候,爲什麼沒有發現而被阻絆着呢?我想是由於担柴時過份的緊張,早已是昏淘淘的麻木了一切的反應,同時沿途的屍體也實在太多,我也就見如不見了。
說也奇怪,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有一種錯覺;覺得我早已死了,當然是死在江中或者是永清寺這一段時間中。現在還在行動的,只是我的靈魂。這種錯覺,一直持續十年、八年之久,好像是等到勝利後才逐漸模糊的。我常常於夜間在床上的時候,自己捏捏自己的手臂,但也自己知道痛。
老和尚:你們活著回來了
快速的跑回到永清寺的柴房,門口的那具警察的屍體,又幾乎絆了我一跤。守志師是永清寺的住持,在灶房裡爲大家燒飯,二空却在佛殿裏打掃散兵的遺物。一見我們終於回來了,他帶一點高興的心緒說:「你們還是活着回來了!」
「要是去送死的話,本應當輪到我和你,而我却代你找了一個替死鬼。」我指指先走進柴房去的老農。鬼子班長當時本是指定我和二空担柴的,我却變更了老農,在那種情况下,我們這個小集團幾乎都是完全聽從我的安排,也許是他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我怎樣的撥,他們就怎樣的動。但老農却始終沒有埋怨我,給他担任了那樣一份可能是一去便不復返的事情。
「我知道,你想幫我的忙,好歹這回你們去的也沒死,可是以後又怎樣?天曉得!」「這種事兒,只能說闖一關算一關了。」「你看那個警察。」他的手指向着躺在廟門的死屍。「你沒有看見,沿途有的是。」「我怎麼沒有看見!就在我們這六畝地的廟園四周,就有46具。」「46具!」我叫着。
永清寺周圍都是石榴園,在這六畝多地的石榴園中,就有四十六具被虐殺的屍體,那是多麼一件觸目驚心的事!
守志師爲我們做了一頓飯,當然談不上有菜,可是這是我24小時後第一次得到的補給。略事安定,也才知道有點餓。在吃飯的當中,我將担柴去的情形告訴了大家。從我拿回來的米和香菸來看,對我們這一羣人,不應當再有什麽惡意。大家的判斷,難關已經過去了,或許不會再有對我們過不去的行爲。
「還不敢說,」我對大家表示意見:「我相信今晚還會有巡邏部隊來的,所以第一我們不能關門,第二我們點着油燈,免得鬼子看不清楚亂開槍。」
大家都覺得我最有辦法,當然不會有人反對我的發言。當我拿出鬼子班長送我譽牌軍煙時,只有守志師是抽煙的,所以我只取了一支外,整包的都遞給了他。我說:「師傅!你留着抽罷!」守志師沒有推裏的接了過去。他問我:「你叫什麽名字?」
我的法號叫二覺
「師傅!你還問這個幹什麼?」我實在不想告訴他我的眞名姓。「那我們總得替你取個法號,才能叫你。」「我看替他取個名字就叫二覺。」瞎子的守印開了口。「二覺,那兩個字?」我問着。
「既覺其生,更覺其死。他叫二空,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我們下一輩的排行是二字。」「那太好了,我就叫二覺,阿彌陀佛。」「你就做守志師的徒弟,我已有了二空。」守印師扁着嘴說,因爲他滿嘴沒有牙齒。
「那你快向師叔嗑頭。」二空在旁邊慫恿。「師傅!請你收我做徒弟。」我當然見機行事,那有不照辦的道理?守志師用手牽了我一把說:「不用行大禮,以後再爲你開香堂。」「人家也不眞當和尚,你還要人家受戒?」八字鬍鬚的老施主笑着說。「不!施主,你看今天這類浩劫,我們還不看穿?要到什麼時候!」我對着施先生合掌行了一個禮。
「二覺有善根,他眞是佛門弟子。」守志師傅對我的印象完全變了。「我們不都吃過糧的麼?現在已皈依了。」守印師和守志師雖是和尚,但也都是吃糧當兵出身的,所以對我肯做和尚,異口同聲表示贊成。
「師父眼睛也看不見,你看看二覺像不像一個做和尚的人?」二空和他的師父頂着嘴。「我當年帶你一同做和尚的時候,未必也像個做和尚的人?」守印師反頂了回去。
我當時還不知道各人的背景,在這兵荒馬亂的當中,我只要能適應環境,能安渡難關也就够了。儘管心理上也有些好奇:什麼都是些吃糧的人,什麼帶着二空一同做和尚?但是我却不敢深問,生怕問出紕漏來。然而我却非常的担心,我這一個假和尚,頭上又沒有香洞,豈不是給人辮子來抓?
好容易闖過了第一關,但是還是難關重重!素無一面之緣,又無金錢的利誘,全憑着佛法無邊的因緣,就可以生死與共,豈不是過份的迷信,所以我只有扛着國家的招牌來打動他們。「兩位師傅!」我叫着:「你們剛才說過,過去也是吃糧的,請看!今天這一場簡直是阿鼻地獄。國家到了這個程度,我們當兵的還能幹什麼?只有放下屠刀,雖然不能立地成佛,也就可以懺悔了。」兩位老師傅都同聲歎了一口氣。
「你多大年紀?」施先生無動於衷的問道。「二十六,民國元年的」「什麼階級?」「上尉連長。」我還是瞞了一級,其實我還兼代那楊厚綵的團附,實際上已是中校了,何况在留法之前,我早已做過砲工兩校的中校教官。
「你很有種,剛才那一場,不是你,我們都應付不下來的。我們得靠你,你安心跟着我們,以後我負責送你過江去。」施先生的話,很帶一點江湖氣。我才安了一點心,但是我還是露了一手說「那是因爲我懂得一點日本話,鬼子說的,我大概都懂,所以比較容易處理些。」
「你會說日本話?」大家都異口同聲的驚訝着。「不!在軍校學外國語文的時候,也學一點而已。」我又有點後悔露了這一手,但却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懂得日本話,至少我比他們高了一層,他們得依靠我。
我們那天晚上一同的躺在稻草裏,我還是精神亢奮得睡不着,但覺得全身都骨頭痛。

我總算苟安渡過淪陷的首夜
一夕數驚,儘管那樣疲累,可是巡邏車在公路上駛過時,小探照燈光線的透入,都使我不能安睡。我望着那小木桌上一燈如豆,和那些縱橫在稻草上的同伴們,我一面恐懼着當夜可能發生的遽變,一面担心未來的後果,恐懼和孤獨同時侵襲着我,而夜深的寒氣,一床與二空相共的薄被,更使我混身發抖。
所幸敵軍的巡邏車,並沒有作沿江的掃射,整夜也沒有再侵入廟門,總算苟安的渡過了淪陷後的第一夜。
守印、守志兩位老和尚隨時都在咳嗽;施先生在夢寐中常發出歎息;二空不斷扭動着身體。一層稻草,舖在黃土地上,蓋的僅是一床相共的薄被,雖然大家都不敢寬衣解帶,一齊都是和衣而臥,可是廟門既沒有關,柴房亦未閉,嚴冬的江風,破曉的寒色,誰又能入睡呢?
比較睡得好的,恐怕要算那位老農。斷續的鼾聲,隨時都在侵襲我們的思潮。
天還沒有粉亮,守印師叔——我已算是守志的徒弟,所以應當稱呼守印爲師叔,突然的叫我:「二覺!你能不能幫幫忙,讓我解一次小手?」
我當然義不容辭,因爲他是一個瞎子;我就一翻身的站了起來。但如何才能幫助這位瞎子師叔解小手呢?我正想發問,守印師叔已經先有所感應的說:「在那墻邊有一個馬桶,你提過來扶我坐上去。」
我照他所吩咐的提了過來,木製的桶,這是江南一帶的便器,紅漆早已剥落了皮,桶蓋也已裂了縫,我一開開,裏面早已積存了半桶糞便,一股臭氣,撲鼻而入。
我扶着守印師叔,幫助他坐上,我站在他的面前,扶着他的身體。「你眞好,我們全得靠你,二空雖是我親生的兒子,可是一個不孝的東西。」守印師一面嘩嘩的小便,一面向我嘮叨着。我沒有敢回話,我當時還弄不清楚他們既是師生而又兼父子的關係。
「師父!你又在說我的壞話。」二空根本沒有睡着,不過是懶得爲他的師父提便桶而已。「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解手非要人幫忙不可,幸虧有二覺來了。」守印師扁了一扁嘴,又歎息了一聲。
「那你昨晚爲什麼不收他作你自己的徒弟?」二空翻了一個身,拉了一拉那床薄被,現在他一個人可以享用。那本是他個人的,而昨晚却分了一半給我。
「啊呀!師兄!」我不得不開口了。「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還有心情來鬥嘴!」「是他一天到晚找我的麻煩!」「我雖然昨天還是外人,現在總算是師兄弟了。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切讓我做好了。」
「你讀過古書?當兵的。」守印師率性解起大便來了。「師叔!請你不要再叫我當兵的好不好?我現在是小和尚,你不也吃過糧的麼?現在是老和尚,都一樣的。」「……」守印師抿着嘴微笑了,接着又歎息了一聲,我知道我掀起了他的回憶。
「天快亮了,大家都起來,等一下鬼子又會來。」守志師傅坐了起來,摸摸他的山羊鬍子。
我伺侯守印師回到稻草堆裏之後,他盤脚坐着——但駝着背,不是坐禪的姿式。「師兄!便所在那裏?我也得去放一放。」我問着二空。「就在這墻的外邊。」他向着東壇一指。
當我拉了一拉僧衣的斜領正要起步的時候,他却制止了我。「且慢,二覺!順便帶着那馬桶去倒一倒。」
這是他第一次指揮着我,我當然是極其樂意的有事弟子服其勞;不過多少有點反感,只覺得二空實在太懶,總算找到了像我這樣一個替身。
提着馬桶,彎過了東地找到了茅坑。可是又是一具觸目驚心的屍體,橫在茅坑的前面,只距離三、五尺遠,正擋着路。那具被刺刀所刺殺的,一灘紫色的血潰,染在灰色軍服的胸脯上,齜咧着牙,半斜着眼,眞是死不瞑目;形態比那廟前的警察更難看。
我躊躇不前,而又進退維谷。但一橫心,自己對自己說:有什麼可怕,我若橫在這裏不也是和他一樣的。
當我正提着馬桶,想從他頭部跨過去的時候,我停住了,覺得這樣對死者太不恭敬,結果還是從他的脚邊繞了過去。(十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