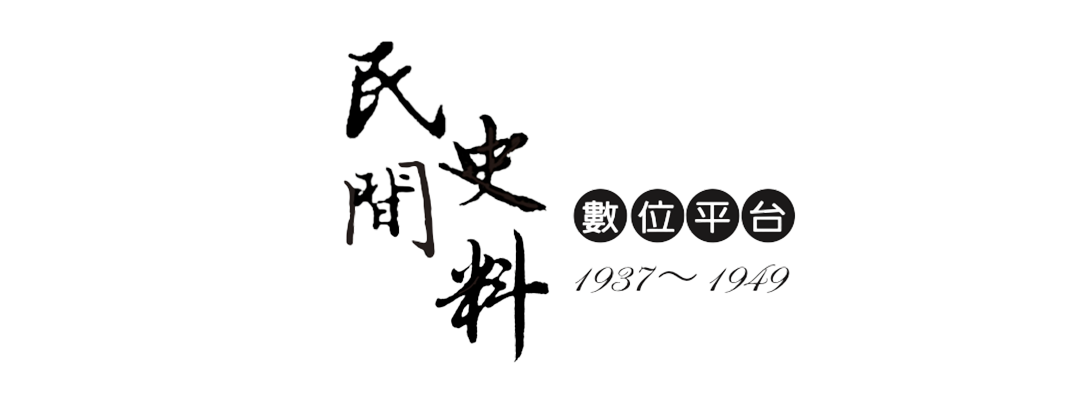本文摘自鈕先銘著《還俗記》,中外圖書出版社於民國六十年出版。

系列其他單元:1
文/鈕先銘,李莉珩編輯
圖/廖文瑋翻拍
前面我曾敍述過永清寺的柴房裡,坐着一位瞎子的老僧,他的法號叫做守印法師。他與二空在出家後是師徒,出家前則是父子。守印法師原是湘軍出身,在庚子年間,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爾後的北平)時,他正是守軍中的管帶(營長),與我守南京時的官職完全相同。在北京城破後,他也有過一段艱危的經歷,所以當我請求二空賣給我僧衣的時候,二空打量了我一下,還盤問了一些小問題以後,便去請示他的師父守印法師。
二空的請示,引起了守印師的回憶。據守印師爾後對我說:由於二十年間的盲目,雖然失去了視覺,却養成他極其靈敏的聽覺。經旬的槍砲聲和一夜間的退守,他縱然未能親見,但聞之甚詳。正當他悲憤着國家的垂危,又間溯着往事的悲傷時候,聽到了我在柴房門口和二空的一段對話,所以他沒有等二空詳述我的來意,他就馬上對二空說:「收容他,拿我的僧衣,給他換個徹底。」
守印老和尚對我的要求,承諾如此之快,決心如此之堅,完全是基於他對庚子年的回憶,所以他當時並沒商之於另一位老僧:他的師兄守志法師,當然他更不會徵詢柴房其他兩位居士的意見。假若他當時稍微猶疑一點,再問問大家,那麼他們決不會收容我這樣一個當兵的人。假若他們眞是普渡眾生的話,也不一定輪得到我,因爲在我之前已有過許多的士兵曾經提出過各種要求。
守印師和二空是來自城内的雞鳴寺。在雞鳴寺與北極閣之間,戰時構築了一座通信系統用的防空掩蔽部;事關軍事機密,一經開戰,早就封閉了雞鳴寺,以杜絕遊人的來往。所以二空師徒二人,遠在兩三個月之前,便寄錫在南京市上元門的永清寺裏。以身份來說,他們是來掛單的和尙,永清寺一切的主持,是屬於守志法師的權限。


鰥居的老農是守志師的鄰居,另一位老先生是永清寺的施主,那兩位優婆塞(梵語,男信徒)的寄居,都是先獲准於守志住持。根據廟宇的清規來講,守印師與二空和尙根本沒有收容我的權利;好在守印與守志兩位大師,在家是同鄉,出家是佛門師兄弟,所以守印師的果決,並沒有遭受到守志大師的激烈反對。可是他從心裡是不太贊成的。
出家前曾從軍的瞎子和尚幫大忙
可是普渡眾生是佛門的信念,所以守志師還是抱着對我同情的心境。萬想不到後兩天,我便皈依爲他的弟子,而且爾後我脫離虎穴,也是他護送我去到滬濱。
二空對我非常親切。當我爲了顧慮空襲,在江邊的竹林裏睡了一覺回到柴房以後,他雖然有點埋怨我不該離開廟子,但是他接着問我:「你餓不餓?這裏還有冷飯。」
自從昨晚六時以後,約二十個鐘頭之間,可以說是滴水未入;要是也算是喝過水的話,那麼就是昨夜掉在江裏,曾經喝過幾口江水。可是我並不感覺得飢渴,在竹林中一覺之後,體力也許恢復了一點,但精神仍然是不能鎮定。二空既然問到我,於是我就反問他:「你們吃過了中飯麼?」
「那裏!你看怎樣的法?」他說着,同時用手指指柴房外的散兵,接著又說:「我們的飯是昨晚煮的,當時還不知道會打敗仗,所以根本沒有準備。」「我也不餓。」我倒不是客氣,眞是一點食慾都沒有。
在三點到五點這兩個鐘頭之中,柴房外面也許還是有許多士兵嚷嚷着,可是柴房内的我們六個人,幾乎是窒息到鴉雀無聲。大家沒有交換過一句語言,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等待敵軍來臨,如何來渡這一關?
柴房外的士兵們也漸漸降入低潮,渡江既不可能,午飯也已經吃過,率性倒在地下睡覺。
我端了一把小木櫈子坐在柴房的門口,可以觀察着;當然是外弛内張,一直是豎着耳朶在聽動靜。
天氣突然開朗,太陽光線從雲縫中射將出來。「敵人來了,是從上元門方向來的。」瞎子和尚守印師突然叫着,眼瞎卻耳聰;等我們都聽到皮鞋的聲音,至少是在守印師發覺的十秒鐘以後。
鬼子兵來廟裡亂槍掃射
果然一隊的皮鞋聲逐漸接近,但並沒有跑步的模樣。接着就是一陣亂槍聲,子彈掠空的吼哮着,我馬上撲向稻草堆裏,和那五位僧俗一同趴在地下。
等到皮鞋聲到了廟前的廣場時,槍聲忽然中斷,繼之而起的是洋人腔的中國語:「來來!」這聲音斷斷續續的叫着。
「碰」的一聲,很重的皮鞋踢在柴房的門板上,其實柴房的門根本沒有關;一個戴著鋼盔的鬼子兵,用已上了刺刀的槍在房門口向上劃了幾劃,也叫着:「來來!」同時還用日語吼着「來」。
我馬上對我們這個小集團的人說:「我們都得出去。」我沒有時間向他們說明理由,這柴房裏太黑,又值夕陽西下,鬼子兵從亮裏向黑地看,當然看不清楚,可能一發狠,拋一個手榴彈,或者是一排亂槍,那就糟了;所以我要大家都出去。
我站起來,順手先將木板窗撑開,使鬼子兵對柴房裏能一目瞭然,然後我扶着瞎子和尙陸續的走出柴房。
來的僅不過十來個鬼子兵,這不過是一般人馬,雖然武裝齊全,但沒有戴階級,僅在胸襟前綴了一塊紫紅的絨布,以代替部隊的符號。從服裝上來看,十人之內沒有一個是軍官,僅有一年齡稍大的班長。他指揮的叫着:「敎他們排列成隊。」
這是用日語指揮着他的兵,我當然聽得懂,我馬上對我們的人說:「我們站到這邊來。」
因爲廟子的內外,至少還有數十名我們的老總,鬼子兵正指揮着他們在排隊,聽不懂話,在用槍托推動着。我指使我們的小集團站在另一邊,我是想表示我們這幾個人不是散兵。
散兵集合好了,鬼子在每一個人身上摸摸,大概是搜索有沒有帶着武器。當然這些士兵早已將槍丢了去。
檢查倒也並不十分的太嚴格,馬馬虎虎摸了一摸,就將隊伍整理好。鬼子的班長馬上轉過來看我們,我扶着的是瞎子守印師,鬼子望望他,又回頭看看廟裏倒在地下的菩薩,他用日語叫了一聲:「這都是和尙呀!」
聽到了這一句日本話,我的心才定了下來,因爲鬼子們已經明瞭了我們這一羣的身份,在沒有處理那一大堆散兵之前,至少不會對我們這幾個人先來一頓亂殺。
前後雖不過十幾分鐘,可是緊張的情緒,使得每個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並不例外,但我必需故作鎮靜,我還得照顧着我們這個小集團,大家也不期而然的聽從我。我意識到只要有一步之差就會出亂子,我必須把握時機來渡過這第一道難關。
守印師是我扶出柴房的,我當時並沒有特別的用意,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鬼子班長第一個就檢查瞎子和尙,連他的眼皮都被摸了一摸。七十老翁,貨眞價實的瞎子,鬼子班長的警覺性已經走了下坡,對我這扶着瞎子的小和尚,連看也沒看,摸也沒有摸。第三位是守志師,也是七十老人;第四位是二空,矮小文弱得不堪一擊;第五是那位老農,當然也不在話下;第六是施先生,那兩撤仁丹鬍子就先惹起了注意,可雖是高頭大馬,但已有古稀的年齡,一套袍子馬褂,繫褲腿而為白襪粉底鞋,橫看豎看也看不出是軍人來,所以倒也輕易的過了關。
穿大衣的中國警察被揪出,遭日本兵槍殺
我們本來只有六個人,三僧兩俗、加上我一個假和尚。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突然末尾增加了兩名,一個胖胖的穿着黑大衣,一位瘦瘦的穿着長袍子。他們大概看見了有非士兵的行列,所以也就站到我們這一邊來。
鬼子班長先拉開那胖胖的黑大衣,裏面是一套警察服裝,這與日本的警服是大同小異的,鬼子馬上叫:「是一個警察!」
照理那一隊散兵都還沒受到虐殺,一個警察也沒有什麼大了不起,至少總不是直接參戰的士兵;可是那位警察實在太沉不住氣,太慌張了,便大叫起來:「我不是的!我不是的!」
言語隔閡,心理變態,敵我之分,勝敗之別;鬼子班長舉起了三八式的步槍,倒過頭來用槍托甩向那警察的腦門子,當然馬上就頭破血流。被打擊的人後退了兩步,鬼子反過來,一扳機,「碰」的一槍,那位警察便應聲倒地,再沒有一點動靜。這是我在淪敵後親眼看見的第一個被虐殺的人,俘虜的下場,誰敎我們打敗仗!
最後輪到那穿袍子的細高中年人,照我看來是當地的老百姓。只因爲穿了一雙黑膠鞋,那與當年國軍的軍用鞋相類似,便被推到那散兵的行列裏去。其後果如何,我雖不知道,但可想而知已被列爲戰俘。
鬼子班長檢查人員完畢以後,便拉着二空走進柴房,由於事前我已將木板窗撑起,鬼子對於內部的情形,自可以一目瞭然。二空被拉進去的時候,自然是嚇得面無人色,我們也擔心着吉凶未卜。還好不到一兩分鐘,鬼子就又走了出來,對一個日本兵說:「裏面有木柴,我們抬一點去燒飯。」
日本兵馬上指使了幾個俘虜兵,抬出了一大堆,可是沒有繩索,也沒有扁担,無法拿木柴歸攏在一起。他們將遺散在地上的中國軍服,用刺刀撕割成布條,然後又找了幾根較長的木柴來做槓子,這才勉强的結成了五堆。鬼子支使着八個中國兵抬了四堆。還剩了一堆,鬼子班長就指着我說:「你們兩個和尚來抬。」怕我不懂,又用手比劃着。
我當然是懂的,鬼子指定要兩個和尚抬,那只有我和二空了,守志師實在太老,守印師又是一個瞎子。我當然賴不脫,可是我沒有要二空做;因爲二空儘管是瘦弱,到底還是太年輕,這不足以做我的掩護,所以我挑選了那位老農,他是年老而又有力的。一老一少,比較對我的形勢有利。
有的是士兵,爲什麼一定要我們中的和尚來抬一担柴呢?我當然百思不解。然而我又怎有資格詢問呢?我雖然未被列入兵士俘虜,但仍是淪陷區裏的被征服了的人。
立志不做漢奸、不說日語偷生
我立志不說日語,是我在脫去軍服,換上僧衣時所決定的。我自己意識得很清楚,只要我不死於亂槍之下,日語是我最好的護身符。那很簡單,一個會說敵軍語言的俘虜,爲敵軍所重視,何况我還是敵方軍事學校出身。
會說日本話的俘虜,輕則可以做通譯,中則可以搾取情報,更重的則可以利用爲傀儡或漢奸。前兩者我都不怕,通譯無傷大雅,既已陷敵,能有溝通言語的人,也許還可以免除許多淪陷區中不期而遇的麻煩。情報,我當時的職級很低,知之不多,逼也逼不出來;最怕的倒是怕要我當漢奸。
從清末以來,一直到了九一八事變前後,進過日本士官的中國學生,總數雖不到一千名,却集結了中國內戰人物之大成。其中固不乏革命元勳,但却也有許多搗蛋份子,所以在內戰中,常常有同學打同學。日本軍方早看穿了這一點,所以對於踩進了士官學校門的中國學生,就無所不用其極的來拉攏;無非是小則以增加中國的混亂,大則極力培養漢奸。
以我自己身經其事來說吧!在士官畢業的成績,名列在三分之二以下,頭尾三年的在學期間,就告過將近一年的病假,這當然不能算是一個優等生。若以才華而論,我那裏值得日本軍人所重視?反不如說是落得他們所看不起。可是當時在陸軍省(卽陸軍部)和參謀本部的少壯軍人,有許多人都和我做過密切的朋友。例如說爾後侵華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隴海鐵路打擊我們最烈的原田熊吉,以及抗戰末期的華北軍司令官根本博,當時都是日軍少壯派的中堅份子。
以年齡上來比較,我當時才十八、九歲,比上述那些日本軍人都小上一倍。以階級來說吧!我是一名士官候補生,戴的是日本中士的階級,比他們中大佐(校官)小了個十級八級。那些日本軍官爲什麼要那樣的敷衍和拉攏我呢?當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像上述的日本軍人的做法,倒不光是對我,每一個中國的士官畢業生,或許都有這種經驗。可是他們對調皮搗蛋的學生却特別的欣賞,規規矩矩用功讀書的人,反而不太重視,例如說,曾經當過台灣省政府委員的朱文伯學長,就是高我一期的軍刀生(畢業名列第二,獲軍刀獎)。可是我相信他沒有我認識的日本爛仔來得多,因爲日本軍方當時認定了我是一塊做漢奸的好材料。
然而我却要使日本軍人看走了眼,我在南京淪陷後一共做過八個月的假和尚,幾乎每天都得和日本官兵周旋,可是他們將刀架在我脖子上過,我也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其原因就是不甘心當漢奸。我很知道,我只要向一個日本的官兵,用一句日本話說:「我是你們士官的畢業生,我和你們的土肥原賢二都是朋友。」我相信聽見我說這句話的日本軍人,一定是驚駭得來屁滾尿流的將我恭送到他們的高級司令部去。
我不用押解而用恭送兩個字,並不是我吹牛,因爲日本在戰時從十七個常備師一下擴充到近百個師團,一般下級軍官,都是幹部候補生(等於我們預備軍官),對士官出身的人,看得比老子還要尊重,何况我還是侵華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朋友!
其後果是如何呢?一定是在利誘威脅下去做漢奸,除非我不要性命。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不暴露身份,所以我在淪陷區的八個月之中,我始終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
脫險歸隊後,許多愛護我的親友都譽我爲忠貞之士,我覺得那並不是給我最高的榮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並不是一個最高的標準。戰爭是一種綜合藝術,要有極高的智慧,才能進入到那個領域。這八個月中我能够和日本軍人耍,耍得他們始終沒有認出我來,這才是我最得意的事。
1964年9月31日,當年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少將,曾發刊了一本回憶錄。其中對我在南京爲僧的事蹟也寫了一大段,不過還是偏重在我婚變的故事,至於我如何才避免了日軍的耳目,僅僅的只附帶了一筆:「占領之後的混亂告一段落,日本軍的官兵常遊雞鳴寺,與鈕氏相邂逅,但終未感覺異狀而避免發現。」(原書268頁)
日本軍知道我在南京的那一段事,並不是在戰爭結束後才揭曉的。在民國31、2年間,紐約時報曾經爲我來了一大段專欄特寫;這個記載馬上被日軍編入了人事資料。所以今井在他的回憶錄裏又寫着:「我們對於鈕少將的極其傳奇性之經歷,已於英文報紙上讀到。戰爭之殘酷,其對於人生影響之鉅,自不得不使我們加以反省。」
從上述一節看來,日軍對於我在南京的那一段,是曾經加以重視的。假如我一念之差,爲了說一句日本話而暴露了我的身份,其後果眞是不堪設想,恐怕我早已無顏來寫這一點回憶以告慰讀者諸公了!
可惜凡是一談到我這段故事的人,馬上都連想到所發生的婚變,對於我爲什麽沒有被日軍發現的眞相,很少有人提及,於是我眞正的中心思想,也被愛我者所忽略。只有兩位長者深切的了解我,那便是楊宣誠和鄭介民兩位先生。民國31、2年間,我担任對日情報科長,涉嫌於機密文件的洩漏,幾乎將我扣押起來,廳長楊樸公也受到上級的指責,但是樸公却爲我辯護說:「鈕先銘若肯當漢奸的話,現在應當是汪精衛偽府的第二廳廳長,絕不會還來當我楊宣城的情報科長。」
這句話的份量是相當重的,我之所以爾後受知於何敬公上將,而得備員於中國陸軍總部,也是爲了這一句話。那件事不久當然是終告雨過天青,眞金不怕火,無疑是與我無關。(十之二)
系列其他單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