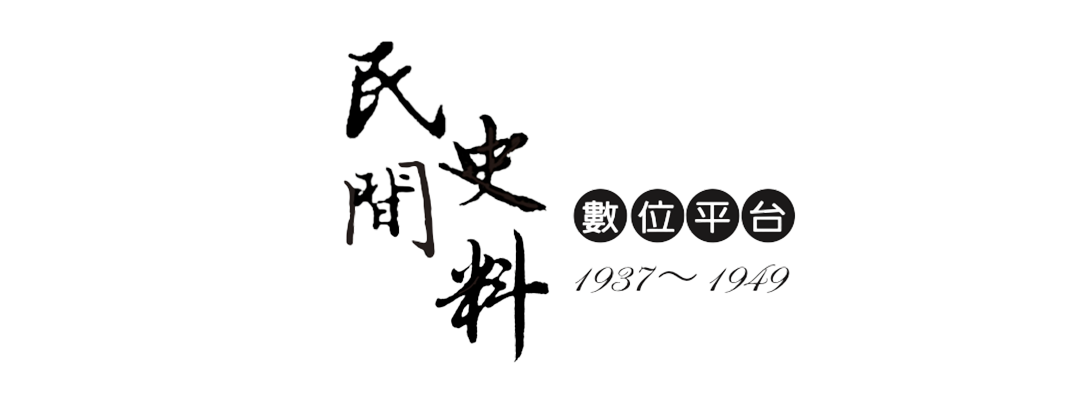系列其他單元:編按
古鑫臺(場員古洪富之父)口述
文/古鑫臺述、孟慶玲採訪
我民國17年2月日治昭和3年,出生在新竹縣北埔山上,家對面的山頭就是五指山。母親彭茶妹生下我一個多月,我父親就往生了,母親生活困窘,因此招贅了我的繼父徐建昌,我還有一姊,賣給別人家,無緣共同生活;父母另外買了一個童養媳,但我和童養媳不來電,後來各自嫁娶。生活很苦,父母作雜工度日,山上很多燒炭的,我爸媽常受雇去挑炭,從山上挑兩三個鐘頭,走到北埔,很辛苦卻賺不到幾個錢。
記得家門口有一棵大樹,七歲時1935年4月21日,有一天突然大地震了,我抱著大樹,感覺一下子地面好像要撞到臉上,一下子又好像要飛到天上,非常可怕,對面的山裂出一條大縫,北埔街上的樓房全倒,壓死很多人。這就是關刀山大地震,全台死了三千二百多人。

我小時有上學,讀北埔小學,早上天還沒亮就出門了,拿竹筒灌臭火油——煤油——燃火把走山路,通常都十幾二十幾人一起走,有些女生年紀比較大的,有十幾歲了還讀低年級,大家都從天黑走到天亮,到學校都八點多了。放學也是要走三個鐘頭,從天亮走到天黑。家裡點油燈,早早睡覺。記得四年級的日本老師叫做本田先生,是個剛當完兵的年輕人,我小時候很「盧」,常打架,就常被先生罰站。
因為家裡窮,沒鞋穿,跑山路腳都凍得紅通通的,父母很心疼我,特別給我買了一雙包到腳踝的布鞋,我也捨不得穿,都是用鞋帶綁著兩隻鞋,掛在脖子上,到校門口才穿上;放學時,一出校門就脫下來又掛在脖子上,依舊打赤腳跑回家。
還記得那時保正常會帶著日本人上山來搜物資,有3隻雞就要拿走2隻,3頭牛就要牽走2頭,連飯鍋都要掀起來查有沒有放番薯籤,不准吃白米飯。記得有一次爸爸買到2斗米,每天早上拿一點出來煮番薯籤飯,然後就要把白米拿出去藏,晚上才敢拿回家,就怕被搜走。
11歲時與北埔山上七八戶人家一起搬家到花蓮南平,坐巴士從蘇花公路過來,路很彎曲危險,開車的日籍司機一路叮嚀頭不可伸出車外,說會撞到山壁。到了南平,是糖廠的地,爸媽自己在地上蓋草房來住,一颳颱風,房子就吹跑了。爸媽平時幫「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砍甘蔗,砍一天領兩角半,媽媽也有種菜去賣,我長大一些也有在苗圃工作,幫忙育苗種樹。

記憶中日本人很重視清潔,規定一年有兩次清潔週大掃除,牆壁、門板、桌椅,都要拆下來洗刷,棉被要晒,都會有人來檢查。
14、15歲時得到馬拉力亞 -瘧疾,每天準時發冷發熱,一發作時就跑去樹下蹲,把時間熬過去就沒事,公所可以拿藥,這種叫作奎寧的藥,吃了全身發黃,但幸運都康復了。
16歲時日本政府派保正送紅單到家裡,我被徵兵到海外,當時說是要去菲律賓打仗。我叔叔那邊一個堂弟是第一梯次的,一到菲律賓就戰死了,我是第二梯次,先上火車,車上全是十幾歲的青少年,我們被送到國福的青年訓練所,做軍事訓練半年,學打槍,我的槍法很準,是第一名呢!記得那時在訓練所都吃糙米飯,一人一碗,吃得正香的時候就沒飯了,吃不飽;也有菜,用大桶裝大豆煮蝸牛,好吃極了!
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後跑警報躲轟炸是經常的事,聯軍的航空母艦停在外海,飛機四、五十架飛過中央山脈,要去西部丟炸彈的印像還很深刻。
在國福訓練所的時候,一次被派去顧守碉堡,剛好遇上轟炸,看到飛機丟下炸彈,炸彈上張開一副小降落傘,卡到火車沒有爆炸,是一顆啞彈¹,沒有傷到人。
另有一次,鳳林分局那邊有兩姊妹被炸死,訓練所的小隊長派我去清理屍塊,也算是軍中的一種訓練。當時我是拿畚箕去裝,非常的慘!
訓練所完訓之後下部隊,到左營當班長,每天考槍法。我只要聽聲音就知道準不準,那時是有領軍餉的,一個月日本錢28塊,在外面一碗麵就要賣3塊錢,算起來很是微薄,根本也不夠拿回家貼補家用。
在等待上船去菲律賓的時候,戰爭結束了,日本長官說你們自己的祖國會過來照顧你們的,你們以後都會有很好的發展。
戰爭結束了,有些日本人還來不及走,阿美族、太魯閣族,和一些高山族,都拿長刀在路上行走,在無政府狀態下趁亂大殺日本人。

國軍來台接收之後,又引起二二八之亂,鳳林的張七郎醫師,是花蓮很有名望的優秀人士,一天夜裡,連同兩個兒子被白崇禧的軍隊帶走打死了,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民國38年推行「耕者有其田」我們有了五分水田,九分旱田。農人不好當啊!收成是半年才一次,日子卻是每天都要吃,那時買東西都只能賒帳,等有收成才有錢還。平常削甘蔗、作工、種田、施肥、換工,作個沒停。
22歲經媒人介紹北林的姑娘彭玉英,以前在鳳林看野台戲的時候有見過面,雙方父母都有中意下,我爸媽賣了幾塊地,她穿白紗,我們租了兩人抬的小轎子把她娶回來。她幫我生了很多小孩,後來有養大的共七個,四男三女。
民國51年我在水璉山上幫林務局開墾林地15甲,和太太英子兩人抱著出生四十天的小兒子,一刀一鋸開山,開出來的地給林務局種新的樹種,沒有薪水,但可以利用林地種菜、種水果。我自己用原木蓋房子住,也種梧桐、香茅、橘子,橘子收成時,挑下中興部落的竹橋到鳳林去賣。小孩子們假日也都跟在山上,上學時就都下山在南平跟著爺爺奶奶住。我在山上15年,山地因為過度開發沒有輪休,地力不夠已經種不出好的水果,也賣不到錢沒有收入,才想要離開這片土地。
民國66年,經朋友介紹,搬到慈惠三街王母娘娘廟附近住,作板模建築業,小孩都已長大,他們小學畢業就到台北去工作。我和英子早出晚歸,工資很多,生活也有改善。但有一次在舊遠東那邊工作時摔下來,腳板整個翻轉過來了,我自己用手把它翻回去,還好能走,但常常會痛。我爸媽也搬到這邊跟我們住,在這邊養老。我日常除了做板模工,也就近在廟裡幫忙煮食,早上四點多就去煮,英子也都跟著我。
大兒子古洪富是職業軍人,民國63年從軍中退伍,因為有戰士授田證,民國85年就在光華分到一塊地,自己蓋了房子,我把水璉山上的權利金賣掉,慈惠三街的房子也賣了,跟著兒子來到光華。兒子在光華六街開「老古牛肉麵」,我也跟著幫忙了一陣子。

英子小我一歲,個性很柔順,一輩子跟著我吃苦打拼,我做什麼,她都默默跟著做,這都是她的命啊!她85歲時往生了,那時常說肚子痛,人也懶懶的,檢查說是腹膜癌,她不肯治療,病了三個月就走了。
我年紀老了之後,二兒子古洪鎮從工廠退休,專門照顧我,女兒們也輪流回來顧我。他們曾討論要請外傭來照顧,我說:「我一個人養你們七個,都養大了;現在你們七個,顧我一個,用得著外人插手嗎?」幸好兒女都孝順,不曾違逆我的意思。
回頭看我這一生,很是驚訝年輕的精力不知是從哪裡來的?英子最常說的話就是:「要打拼,才有飯吃。」我拼命工作,記得在水璉山上,花生、玉米成熟時,用大布袋裝,我一天要扛四五十袋,從園裡扛到工寮,曬乾,再扛下山賣。現在92歲啦!以前眼睛一睜開就是工作,現在吃飽免做啦!即使有工作也沒法度作啦!每天早起在門口走走路,有子有孫,很滿足了。
我父母只有我一個獨子,千辛萬苦拉拔我長大,英子懷頭胎時就懷了雙胞胎,但整天跟著我工作,還蹲著割稻,雙胞胎就流產了,母親擔憂我子嗣不繼,於是在48歲那年開始吃長齋,祈求我能開枝散葉,人丁興旺。英子跟著我吃很多苦,成功生育七個孩子,唉!都是過去的事了,再說也無用。我和她相隨一世人,不曾吵過架,更不要說不曾打過架,我做什麼她都跟著做,她做什麼我也跟著做,不停的工作,到晚上才聊聊天,說說笑,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感情,不用說出嘴,我們彼此心裡都明白的!﹝109.4.11定稿﹞
採訪後語 孟慶玲(111.7.29)
當初社區理事長石福春興高采烈要帶我去採訪古伯伯,我立刻提出重大問題:「哪一省的?說的話我聽得懂嗎?」因為之前採訪太多南腔北調的老兵,我是吃足了苦頭,所以一定要先請子女在場當翻譯,否則就像鴨子聽雷²啦!沒想到理事長很輕鬆的說:「台籍,沒問題!」更沒想到的是:不但是台籍,當的還是日本兵呢!在光華這太異類了,完全顛覆我的頭腦。
原來古伯伯是台籍客家人,幸好他沒用客語講,因為我雖是客家媳婦,但學客語完全不及格,聽不懂啦!還好老先生一直用緩慢的閩南語敘述,這是我的母語,自是溝通無礙。
對於花蓮的客族,感覺人數非常多,簡直可和原住民平分秋色,原以為是光復後才形成的 ,聽了古伯伯的故事才知道原來早在日治時代就有集體的向東遷徙。
古伯伯成長在台灣,經歷日治時期,因此當上日本兵,與農場中打共產黨的老兵,年齡雖然相仿,經歷卻很不一樣,但都是走過戰火的苦命一代。
但古伯伯怎會在光華農場呢?原來他的兒子是年輕的場員,他跟著兒子過來的。農場原是為安置追隨政府來台的老兵而設,而民國85年當台籍的年輕場員入住時,就顯示農場的任務已經圓滿,果然再兩年,民國87年農地放領完成,農場就正式功成身退了。
感謝古伯伯的小女兒古梓羚努力促成採訪,我們才能留下先民活動的珍貴紀錄。
注解
¹啞彈(dud)泛指任何在使用時沒有按時或如願產生擊發或爆炸的彈藥。雖然啞彈在使用時沒有產生預期的殺傷力,但是日後很長時間仍然具有延時引爆的風險。(https://zh.wikipedia.org/zh-tw/哑弹)
²(歇後語)有聽沒有懂。
系列其他單元:編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