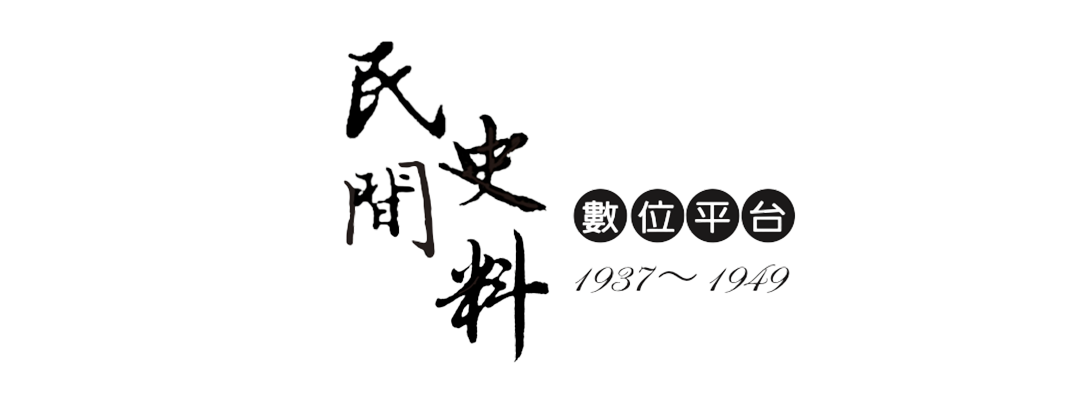本文摘自鈕先銘著《還俗記》,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60年出版。
文/鈕先銘,李莉珩編輯
守志師將昨夜剩下來的冷飯炒了一下,要大家快吃。「鬼子一會兒就會來的,大家快吃,中午我們不燒飯。」守志師很够機警,不愧爲一個老吃糧的人。果眞我們到那天的深夜才吃到第二頓飯。
這回我們將桌子抬到大殿上來吃。說二空懶麼?也不見得,昨晚他就將大殿掃除了一次,今早又在那裏打整。「二覺!我們來將菩薩抬一抬正。」
施先生不愧爲是一位善男子,他要我和他將倒了的佛像扶正。那下面的神龕,早被散兵取去當作渡江材料去了,所以老佛爺就名符其實的垮了台。施先生也順口叫我二覺,這在我又是一種欣慰,我眞的算是和尚了。
「我們不要光抬菩薩,也將那位警察老爺抬抬開好不好?天堂和地獄只隔這一道門。」我指着門外的警察屍體。「不能抬開。」二空提出異議。「爲什麼?」我和施先生都懷疑的問。「萬一鬼子不高興就糟了。」
亡國奴不敢抬走屍首,怕日本鬼生氣
人被虐殺了,抬開都生怕鬼子不高興,這才眞是亡國奴的滋味。誰叫我們貪生怕死,連屍首都不敢抬開。「那還有在茅坑前的一具,多難看。」我還是有點不甘心。「一共有四十六具,我數過了,我們都抬得開麼?抬到那裏去?」「過幾天就會腐爛的。」「不會,天太冷,又在風裏頭,和風乾臘肉一樣。」和風乾臘肉一樣!我吸了一口冷氣。
我只好順從着二空的意見,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還想活着。二空的意見本是似是而非的,可是若搬出了毛病,豈不是禍由我起!
在那以後的十幾天之中,我們一出廟門,或者是上一次茅坑,必須要跨過那兩位無名英雄的屍體。我總是先唸一句「阿彌陀佛」,然後再從他們的脚邊跳過去。我對那兩位先烈,只能表示這一點敬意,我深覺得活人眞是不如死人來得香。
白天倒還可以,有一次夜急,我不得不上茅坑,我面對着那一位,起初倒眞有點怕;可是仔細的想想,我們本是同澤同袍,只一瞬間而人神遽隔,他倒永息了,也許早登天堂;而我呢?却還被遺留在這阿修羅道中,他若在天有靈,應當護佑我,有什麼可怕?
十幾天以後,稍微安定了一點,我還是和二空兩人將那二具屍體移到了江邊去,當然無法埋葬,連想找一床蘆蓆掩蓋都不可得!
我眞的流淚了,經過前幾天那樣的恐怖與悲傷,我都沒有哭過,這一次抬屍,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我眞的是涕淚交流;或許是稍微安定了一點以後,我才恢復了一點人性的感情。在那以前,眼是紅的,筋是暴的,也等於活屍一個而已。
「不用難過了,這是臭皮囊,與他的靈魂何關?我們都是學佛的。」二空安慰着我,與他以前所說的「風乾臘肉」,其心情也迥然的改變了。我呢?依舊是「凡夫迷離」,既不能覺生,復不能覺死,有負我的法名「二覺」。
二具屍體雖然移開了,可是在六畝地的石榴園中,還有44具,我們又向那裏移呢?只好聽其自然。
我們吃過昨晚剩飯以外,不約而同的都坐回敷地的稻草上面。爲什麼呢?大家都等着,等待着鬼子再度來臨。誰也不敢一個人停留在佛殿裏或者是廟前庭院上。人靠着人,要死也死在一塊兒,大夥兒一同盤着腿,好像是一羣老僧在入定。

朝曦從門縫中射了進來,冬風也隨着黎明轉暖。可是我們大家在先前曦微中那一點朝氣又消失去了,誰也沒有肯說話,是誰也沒有敢再說話;越是沉默,在沉寂中越更發生恐怖;越是等待着,而時間也就覺得愈長。
大約是九點鐘的前後,紅日已上三竿,守印師叔又先發覺了皮鞋聲。「就要來了,沒幾個人。」他用湖南腔低沉地叫着。我們都豎起耳朶聽,果然是來了,皮鞋聲音不雜,不像是大隊人馬,來的只有三個人,大概是一士兩兵。
三個鬼子一走進佛殿的門,看見那已扶正的佛像,先就鞠了一個躬,來意倒還不惡。我們從柴房裏,向外看得很清楚;我推了一推二空,輕輕的對他說:你出去應付一下,能拜菩薩的不會馬上就殺人。」二空倒也沒有推諉,站起來走了出去,宣了一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
「是個廟子!」鬼子伍長用日語叫了一聲。他沒有理會二空,却跨前了一步,向柴房裏張望。我早已將木窗撑了起來,大家當然知道我的用意,雖然要忍受着寒風的侵襲,但柴房裏却很明亮。「一共幾個僧侶?」這當然是用日語問的。誰也不懂,二空又落在鬼子伍長的後面,我就不得不硬着頭皮站了起來。
「一共是幾個僧侶?」他又重複的問了一聲。
我何嘗聽不懂,可是我不能用日語答話。於是我就先點着兩位老和尚,再點着我自己和他背後的二空。他似乎還沒有滿足,便將步槍向地上一豎,用手臂夾着,然後從軍衣袋裏取出了一疊軍用報告紙,用一支紅鉛筆寫着:「幾人?支那兵有?」
日軍也愛被拍馬屁
他還沒有寫完,我早已看明白了,我從他手裏要過紙和鉛筆來,馬上也用似中文而又像日文的寫着:「四僧二百姓,皆良民,請閣下保護。支那兵無。」
「馬鹿!俺也成了閣下?」他用日語咕嚕着。在日本軍隊中的習慣,要官拜將軍才能稱閣下,我是故意這樣寫的,一半是討好他,一半是表示我不懂。「馬鹿野郎」是日本人最普通的一句罵人的話,此地他僅用了馬鹿兩個字,我只意譯爲:「胡說!我也成了將軍?」
儘管他嘴裏再罵「胡說」,可是這馬屁還是拍得不錯。他又抽了一張軍用報告紙,還是用紅色鉛筆寫着:「此係寺宇,皆爲良民,應予保護。」
這回他是用純日文寫的,除漢字以外又加了些日本字母。日本人寫的字,多少與中國人所寫的形態不同,兼之又是用的日軍軍用報告紙,當然一看就知道不是偽造。我從他手裏取得這張紙條以後,實在高興極了,雖然明知一名伍長的便條,既無「關防」,又不簽名,那會有多大效力?可是總是日軍寫的,唬唬其他的兵,總有一點用處。
這三個鬼子兵連後院都沒有檢查就走了。
鬼子是要用鬼符治的,一點不錯,那張紙條,果然發生了莫大的效用。從第一批以後,每隔二、三十分鐘必定有另一批鬼子來臨,人數不一,至少是三名,多則十來個人。
每一批,我必定將那張條子給他們一看,同時也必定的大聲恭誦一聲佛號。我故意的將南無阿彌陀佛的陀字,讀成「達」字的發音,因爲日本人唸佛是唸成:「南無阿彌達不子。」
「不子」是在佛字下面又拉了一個語尾聲,而陀字則讀成達字的發音。這本是梵語的譯音,中日兩國唸法應當是相同的,到底是誰唸走了板,雖然我也到過印度和錫蘭,爾後我又到過印度的佛教聖地加雅,但是對梵語幷無考證。
我不敢完全照日本人的唸法來恭誦佛號,我僅僅將陀讀成達字,只要使鬼子兵能聽得更清楚,也就够了。
日本可算是佛教國家,所以十個兵之中倒有七八個見了佛像就會鞠躬,一尊佛像,一聲朗誦的佛號,一張日本兵所寫保護符,不管來了多少批,都一關一關的安全闖過。
有一批大概五個人,照例的巡視了一周,又看了「鬼子符」以後,突然從乾糧袋裡掏出了一包「羊膏」給我,嘴裡唸唸有詞叫着:「心焦!心焦!」也和昨日鬼子班長給我米筒一樣,無非是給我的意思,但我實在慚愧,留學五年,還是孤陋寡聞,不知道「心焦」兩個字的發音,到底漢字是如何的寫法?
這批鬼子走後,當中有一、二十分鐘的間隔,我對大家說:「鬼子還給了我們一包羊膏,誰吃?」「羊羔?葷的,我不吃。」瞎子師叔首先拒絕了。
「不是羊羔美酒的羊羔,而是羊膏。是一種水菓做的凍子,但比中國的凍子硬一點。」我解釋給大家聽。「管牠是葷的素的,讓我來嚐嚐。」守志師傅從我手中接了過去。「我來給你拆開。」
我又搶了過來,撕開包裝紙,找了一根筷子,將羊膏壓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每人都分着了一塊。「師叔!羊膏是素的,而且是甜食,你嚐嚐看。」我特意送了一塊到守印師的嘴邊。
「是素的,我也不吃,我沒有牙齒。」「不硬!你試試看麼?」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塞進他的嘴裏。「不錯,蠻好吃的。」大家都同聲讚許着。「可惜太少,等一會兒你再向他們多要一點。」二空簡直是食髓知味。
「我可不敢!等一會兒,他們再來了,你找一支筆寫着羊膏兩個字,嘴裏再唸着心焦,心焦,他就會給你的。」我調侃着二空。
「二覺眞有種,連鬼子都給你唬住了;昨天的米,香煙,還有羊膏。什麼?羊膏,怎麼寫法?」施先生笑着說。「糕餅的糕字。」「管牠什麼膏字,好吃就得。」二空接着腔。
「丘八吃八方,和尚吃十方,你們都不懂?」守志師吃了一小塊羊羔以後,從衣袖裏取出了昨晚我拿回來的那包香煙,燃了一支吸說:「二覺!你也來一支。」
「我不吸,師傅。」「當兵的不吸煙?」「師傅!你又走了口,我是和尚。」大家都笑了!「和尚也可以吸煙。」「我不是不抽煙的,可是想留給你吸,來之不易。」「不要怕!只要有廟子,有菩薩,又有和尚,總會有施主來孝敬的,那怕是日本鬼子。施施主!你說對不對?」守志師向着施先生笑。
從那天早上起,糊塗的日本兵閣下,寫了一張「應予保護」的鬼符,又吃到了一包羊膏;味納的錯覺,一時大家將昨日的慘狀似乎都忘記了,覺得日本鬼子很好對付似的。
下午三、四點,一輛汽車隆隆的從公路上來了,誰都聽得到,用不着守印師敏銳的聽覺。繼之是一陣皮鞋聲,來的鬼子在十人以上,其中兩人一看便知道是軍官;雖然也同樣的沒有戴階級符號,可是手裏不是持着步槍,而是掛着戰刀。
日本刀自古隨着武士道而出名,但自火藥武器發達以來,日本刀早已變成了古董,僅供愛好藝術品人們的鑑賞,實際上早已失去了利器的作用;可是在戰爭中,日本軍官都將日本刀裝備成軍刀,其用意無非是想發揮昔日固有的武士道精神而已。可是這大半是機器製成的,而不是匠心的結晶。
我一見帶有軍刀的鬼子,當然一望而知是軍官。一老一壯,年齡相差總十歲以上;可是老的似乎反不如少的階級來得高,因爲這一次十人以上的大軍兵臨,像是以這位少者爲主腦。
在日本軍人中,軍官與軍士,其階級觀念是極其分明。一位軍士若沒有加受補充教育的話,很難升到軍官,僅能到準尉階級的特務曹長而止,可是這一批特務曹長却是日本軍中的真正骨幹,在戰時所担負的責任,往往較初出茅廬的軍官爲重而階級也許比軍官要小一兩級。
日本軍官親自來查,這次最難過關
依我的猜測,來的兩位帶刀的鬼子,一個是少、中尉軍官,一個是特務曹長。自從昨晚以迄今日的午後,川流不息的雖然來過了不少的日本兵;可是由軍官所率領的部隊,這還是第一遭。我一看便意識到箇中的嚴重性,然而我們其餘的五個人(三僧兩俗),都是鬼子並不難應付的先入爲主的觀念,因之反而忽視。
這一次擺的架式可大不相同,十來個槍兵分站在四角,端着槍,上了刺刀,手摸扳機,如臨大敵的樣式。
先由一個班長似的鬼子兵,將我們都趕到廟前的庭院,排列在離那警察的屍體不到五尺的地點。先由那班長作情况報告。這班長並不是昨晚首次來過的班長。報告詞的大意是此地是上元門外面江的一個小廟,居住者是四僧兩俗,均已多次的巡視與偵察,似尚無寓藏支那兵的嫌疑。先說明地形其次是敵,在敍述着任務而到判斷;雖然僅僅是短短的幾句話,而層次分明簡單扼要,鬼子兵的教育,眞算不錯的。
鬼子班長報告如儀後,兩位日本軍官少者在前,老者在次,向我們逐個的檢查。我當然仍是扶着守印師瞎子和尙,可是經過我的時候,稍微瞟了一眼就移注其次的人們。而對二空則略事盤旋,可也沒有發問。
這樣順利的通過,我已預感着不妙,但我想或許對我們全體必再有一番審問和訓話。若是基於耀武揚威的心理,那當然很容易滿足他們,即使有些疑問,只要是對全體的,我也有辦法應付,因爲這一日夜之間,我對於同難的五個人,大體已經摸得很清楚,半眞半假的,也未必不可以敷衍過去。在人員檢查完畢了後,兩個軍官商量着要看看廟宇的環境,當他們提出似乎要人帶路的時候,我指指二空,同時又用中國話說:「你帶他們去看看後院。」這也很自然的,在六人之中,只有我和二空年紀較輕,我既是扶着瞎子和尚,那麼再有任務,自然而然該輪到二空了。
他們還沒有起步,我做了一個手勢,問他們我們可以不可以回到柴房去?當然我先指着瞎子和尚,他是我們的擋箭牌。年青軍官點頭示可,我就扶了守印師,而且將其餘的人一同帶回了柴房。
我想這大概又算過關了,鬼子看看周圍的環境,還不打道回衙!那知他們才繞了半個圈子,就闖進了柴房。還沒有進門,我聽到那個老的在說:「我看那個年輕的人就不像是一個和尚。」「我們來盤問盤問他。」少者也附和着。
不知在什麼時候,老者的軍刀已經出了鞘,他一進來就在我的肩膀上敲敲,你說我能不怕麼?當然是嚇得魂不附體,但我還得裝着鎭靜,心想未必就在柴房裏殺我,要殺也得拖到廟外去;何况他們還要再盤問我呢!這是他們在進門前所商定的,何至於不問而誅?可是我知道這一關將相當的成爲難題,會不會非使用我的王牌——日本話不可?我得好好的應付,沉着氣,盡量的不要我最後的一招爲妙。
老者用刀敲敲我的肩,同時伸手示意要檢查我的手。我伸出了雙手,手心朝天,他用手在我的手心四周捏了又捏,這大概是看我的手掌,有沒有起硬繭;當兵的持久了槍,每每有這種現像。但兩位日本軍官,萬沒有想到我不是兵,而是一個官。假若那少者是士官學校出身的話,至少也是我的後輩;檢查手掌,當然難不着我。
其次他又要檢查我的頭部,還是用刀背在我的頭頂上敲敲,先要我脫下那頂僧帽。這一下我可眞慌了,若是要檢查我的戒疤,那不是馬上就會現形,那裏還能避掉?
我想我該用日本話了,那將是圖窮而見匕首的時候;可是我還在作最後的忍耐,只要他不放槍,不耍刀,我總還有餘裕的時間。(十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