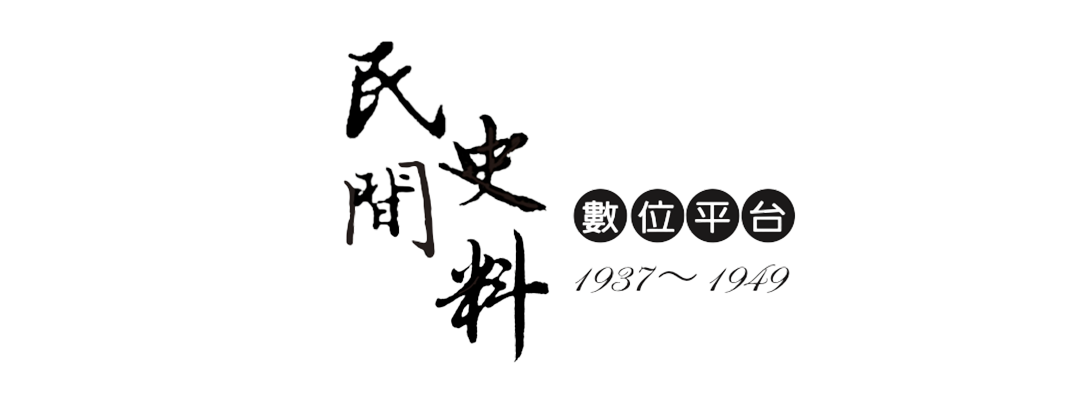本文摘錄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張郁廉,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迅速以武力佔領了華北。當地各大學多遷往後方。燕京大學乃是例外,它以校產及經費均為美國所有為由,繼續懸掛美國國旗,對付日本,藉以維持校務,勿使中斷。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對日宣戰。北平燕京大學即被日軍包圍,宣佈解散。學生及教員被拘押數十人。司徒雷登校務長也被軟禁,直到戰爭結束,方恢復自由。
燕大被日軍解散的消息傳到重慶,燕大校友群情激動,一致決議要在後方復校,遂召開臨時校董會,推舉梅貽寶為復校籌備處的主任。當務之急是解決校址,迎接由淪陷區來到後方的燕大師生。籌備處經權衡利弊,最後仍以成都為首選。理由是成都為大後方的重心,又接近陪都重慶,是四川稻穀的匯聚點。成都講文化,素有「小北京」的稱號,而最有說服力的因素,是成都基督教大學聯名表示歡迎燕大在成都開課,共同營造「教育之都」。四川省主席張群先生及燕大校董孔祥熙先生也大力支持。
我聽到好消息,說1942年(民國31年)北平燕京大學將在四川成都復校,6月開始招生,10月開學(較其他大學遲兩周),十分興奮,向已工作了兩年的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辭職,到成都續讀一年,完成大學教育,以不負父親對我的叮嚀和希望。
離開國際宣傳處,雖然不失為明智,但也經我事先反覆衡量、取捨,畢竟不容易。國際宣傳處在抗戰期間的重要性、聲譽、地位,除了中央通訊社,少有同類機關可與之分庭抗禮,而同事之間感情融洽,猶如處於一個大家庭,同甘共苦,工作、吃、住都在一起。我的工作很有意義、很重要,而我勝任愉快。
國際宣傳處培養出來的青年才俊,以後不少成了國家的棟樑。葉公超、朱撫松做過外交部長,董顯光、沈琦、朱撫松、沈劍虹、淩崇熙、溫源甯、葉公超、邵毓麟、夏晉麟、鄭寶南等人當過派駐各國的大使。在台灣,原國際宣傳處同仁擔任新聞局長的先後有沈琦、沈劍虹、魏景蒙三位。經幾番掙扎,我決定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
辭職手續辦好了,入學許可也得到了。離開重慶前,偶然遇到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我把去成都讀書的事告訴他。他很贊成我的決定,並說:「畢業後回重慶,歡迎你到中央社來工作。」短短幾句話,對當時的我,是多大的一份力量,一份鼓勵!於是,我滿懷信心地到成都去了。
9月底,我在成都就學的前夕,接到繼母托人從哈爾濱輾轉寄來的信。她告訴我,我的父親在日本的統治下,受盡了折磨、屈辱和饑餓,感染了斑疹傷寒。得病後,因得不到良好的營養和治療,於1942年5月在哈爾濱不治死亡,那個時候他還正值五十六歲的中年時。父親臨終時不斷叫著我的名字。每念及此,心如刀割。失去父親,使我悲痛逾恒,我無比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無力和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父親在世時,女兒無法遵循他的意願讀完大學,這是重大的遺憾。如今,哪怕遇上千難萬難,也要完成父親的遺願。多年來,我所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的都是妻離子散或生離死別的人間大悲劇,而這些都是日本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所造成!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華兒女又豈敢稍忘?!

許多年以後,我見到復成弟,他還告訴我一些我遠在四川,和家人斷絕了音訊那十年所發生的事情。父親再三囑咐復成兄弟,假若有一天,生死不明的叔叔回來,一定要把家產分一半給他。復成弟最後一次回山東老家朱由村,是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鄉安葬。那時外婆還健在,四姨父也回來了,四姨生了一個男孩子,和外婆住在一起。而瞎眼的奶奶復明了,我想她患眼疾是當時生活過於清苦,營養不足所致。
文廟權充男生宿舍
燕大在成都選址頗費周折。美、加教會合辦的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校址在成都城外岷江南岸,稱「華西壩」,校園廣闊,校舍壯觀。但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及濟南的齊魯大學,已先後遷到成都,與華西大學合作,共用華大的課室、圖書館、實驗室等設備,並在校園旁的邊緣地帶建造臨時宿舍。華西壩既已「客滿」,燕大只好另作打算,在成都租下華美女子中學及啟化小學的校舍,這兩所學校毗連,地址在陝西西街廿七及廿九號。兩校的師生因躲避敵機轟炸,早已疏散到外縣。兩校對街就是衛理公會禮拜堂和同仁眼科醫院,桂毓即在此醫院實習。
華美女中的主要建築,是一棟兩層高樓宇,內有教室六七間,還有小型禮堂和閱覽室。原來的頂樓、陽臺、過道等,加以簡單裝修,即可辟為辦公室。大樓的前院較小,後院較大,建有三層樓房一座,下層是女生食堂,上兩層是女生宿舍,住進一百二十名女生。我和室友
湖北籍的耿曾蔭住在三樓,室內雙層木板床,她睡上鋪,我睡下鋪,一張書桌共用。耿是由淪陷區來後方就讀的,好像是大二生。我們相處融洽,只是她較懶散,衣物、書籍亂放。有一天深夜,宿舍發生火警,濃煙彌漫,我睡夢中驚醒,急忙穿好衣服,先把被褥、衣服、書籍用床單包好背上手提著大皮箱,由三樓急速走到對街的同仁醫院人行道,再返回宿舍幫助耿曾蔭收拾凌亂的衣物。這一教訓倒使她知道,必須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好。耿曾蔭的男朋友阮某是驅逐機飛行員,他每次出任務,我陪著她提心吊膽,直到他安全返回基地為止。所幸一年多後,抗日戰爭勝利,他們結婚生子。後來我在台灣還和他們見過面。
啟化小學規模有限,校舍用作教員宿舍,每家兩間,梅校長一家也在內。男生和單身男教員則借用離陝西街和華西壩不到半哩的文廟,還算方便。二百多男生擠在各廟室雙層木板床上睡覺,大成殿則用作餐廳,就這樣,勉強解決了男同學的食宿問題。戰時生活越來越苦。成都人口驟增,電力不足,只好分區輪流停電,先是每四夜停電一次,後來每三夜停電一次。晚間學生集中在禮堂,學校發給菜油燈用以溫習功課,但油燈下看書效果不佳。再就是人人營養不良,疾病叢生,醫藥又缺乏。我當時身體瘦弱,極度貧血,低頭彎腰頭暈眼花,甚至暈倒過幾次。多虧成都不是軍政要地,日機很少來空襲,免去跑空襲警報之苦。
另外,成都有我的好朋友景荷蓀、李賦蕭、羅協邦,還有孫桂毓,他們盡心盡意地照顧我。景荷蓀已再嫁,丈夫是湖南籍的營建商何遠經先生,何不到四十歲,為人正直忠厚,婚後生活美滿。荷蓀還在金女大任助教。李賦蕭醫科畢業後,在成都市立醫院做實習醫師,並有了男朋友王培仁,他也是醫師,兩人情投意合,已有結婚的打算。羅協邦由重慶遷居成都,是因為其夫易國瑞調職,到成都郊區新津飛機場任場長。協邦曾抱著一歲多的女兒易榕青到燕大來看我。我畢業前,協邦生下長子易正宇,派吉普車接我到新津住所吃滿月酒。
1937年在漢口馬路上巧遇的韓伯母(韓松林的母親),也到成都勵志社任職,工作與蘇聯空軍有關,免費供應營養伙食。韓伯母經常把她那份早餐中的一隻雞蛋煮熟,自己不吃,帶來給我,戰時能吃到雞蛋很不容易。她的長子韓墨林被派到新疆工作,那邊情勢複雜,到職不久就失去聯絡,從此失蹤,生死不明。那時她的次子松林的工作即將結束,他體格粗壯,身材高大,因年齡、經濟及學歷的限制,無法進入普通中、大學校,我建議他去投考軍校。

回爐當學生
1942年10月1日,在四川成都復校的北平燕京大學正式開課。註冊學生依照預計共有三百名。從北平來成都復學的舊生,無法限制,隨到隨上課。第一學年結束時,學生共計三百六十四人,其中約一百五十名是來自北平的舊生。我和余夢燕雖然來自重慶,但算是燕大的「老舊生」。繳清全年學費五百元後,選好科,住進分配的宿舍,開始上課。交了學費,身邊留下每月的伙食費,至於零用錢,則沒有著落了。幸好我在學校申請到一份工作 ——幫助哲學系施友忠教授上課時點名及批改同學的考卷。
我除選讀了一兩課教育必修課程外,還選讀了梅貽寶教授的《哲學概論》,並和余夢燕選了政治系一門頗難讀但叫座的《國際公法》,是吳其玉教授的課,每週兩次,還要到華西壩和別校同學一起聽課。另外,我選了家政系楊敏嫻教授的《營養學》,對各類食物及各種維他命有了較深的認識,使我一生受益。
在成都回爐當學生,生活雖然清苦,卻是一生中最輕鬆愉快的一年。好友們知道我哪天沒有課,就到學校來看我,不忘帶些食物和必需品。每個週末,我固定到荷蓀家住上兩晚,週一再返校上課。荷蓀的家舒適雅致,在那裡無拘無束,感覺實在好。住所是一棟兩層小洋房,前後有院。每個週六一下課,我就迫不及待地往荷蓀家跑,一進門就聞到燉肉的香味。荷蓀悠閒地坐在客廳火爐旁,一邊烤火,一邊細心燉煮濃郁的肉湯,供我進補。荷蓀永遠是那般善解人意、真誠親切、從容不迫,讓人從心底感到溫暖。學校伙食很差,主食仍是難以下嚥的「八寶米飯」和「炒空心菜」,偶爾有幾片肥豬肉。週一清晨返校時,荷蓀總不忘讓我帶一罐熬好的豬油,每餐往熱飯中加一匙豬油拌醬油,滋味至今難忘!
另外,每天午餐時,學校廚師特別會為我蒸一小碗豬肝,這也是荷蓀看我嚴重貧血而商請校方提供的。何遠經戴著一副金邊眼鏡,文質彬彬,不慌不忙,話不多,也像荷蓀一樣,待朋友肝膽相照,對荷蓀專一,愛護備至,十分顧家。他從事營造業,每日很忙,有自用三輪車一輛上下班,每次他返家時,老遠就聽到三輪車的叮噹聲,這是他先通知家人:我回來了。有一次,我在荷蓀家,荷蓀預備了一桌豐富菜肴,囑咐何遠經早點返家共進晚餐,結果左等右等不見他回來。荷蓀見菜飯涼了,一次一次拿去再熱,端進端出,等得實在不耐煩了,臉越繃越緊,爭吵有一觸即發之勢。不一會兒,遠處傳來叮噹聲,主人回來了。我躲到一角,不想參與紛爭。只見荷蓀態度忽然大變,笑臉迎門,噓寒問暖,端茶遞巾,愉快地招呼大家就座進食。
事後,我問荷蓀為什麼那麼虛假,裝模作樣?荷蓀說:「假若我不忍耐,這頓飯大家還能吃麼?過去就算了,要多為他人著想。」遇到李賦蕭值班的週末,她不能外出,我和荷蓀會帶去肉、菜、饅頭到賦蕭醫院宿舍,燉上一大鍋羅宋湯或大鍋菜,大家又吃又喝又唱,其樂融融!住在學校,晚上餓得發慌,耿曾蔭會帶我溜出校門,到街口攤販處買個燒餅夾豬頭肉或豬耳朵,有時到附近有名的「吳抄手」吃碗豬油拈麵(豬油拌乾麵)或一碗紅油抄手(餛飩),這對我們窮學生來說,是十分奢侈了。
做學生的日子過得特別快,轉眼到了寒假,有家的紛紛離校,學校雖然為無家可歸的學生留下幾間宿舍,但停了伙食,學校裡冷冷清清。我被荷蓀接到她家,住在樓上主臥房隔壁的房間。正趕上荷蓀生產坐月子,她為何遠經生下一個兒子,全家喜氣洋洋。女主人聲明在先,坐月子期間絕不下樓,也不管家務。每日清晨傭人王嫂端來一大碗「酒釀蛋」(加兩三個荷包蛋)給產婦「發奶」,接著敲我房門,送來同樣一大碗「酒釀蛋」,說是太太吩咐的,不能拒絕。如此,整個寒假我陪著產婦,晨、午、晚都在樓上,吃同樣的滋補食物。
荷蓀說一定要把我弱不禁風的身體養壯。每天下午,大家聚在樓上小房間,喝「下午茶」。賦蕭差不多每天都來,享用加糖和牛奶的紅茶,另有荷蓀早就備存的各式小點心。她們總是把最大的那碗熱騰騰、香噴噴的奶茶給我喝。不知喝了多少次,直到有一天我無意中看見荷蓀把她的乳汁擠入一個杯子裡,加上好友們每天喝奶茶時的眼神,證實了我的想法:我喝的是荷蓀的乳!為此,我曾大喊大叫,又吐又嘔。吵鬧平息後,賦蕭說:「人乳最富營養,醫院中多少人想買都買不到。照照鏡子看你現在的臉色多紅潤亮麗,這都是荷蓀的苦心啊!」
寒假結束,返回學校,我確實是精神奕奕,身體強壯多了。再苦讀半年,就要畢業了。這時,對日抗戰已進入第六個年頭,在日偽的全面封鎖下,物資更形匱乏,通貨漸見膨脹,全國同胞艱苦支撐,同學們的生活越來越苦。幸好四川素稱「天府之國」,糧食勉強可以自給。學校當局也費盡心力,維護同學們學業的正常進行和人身安全。
有一天,荷蓀到學校來看望我,我拿出一雙灰藍亮色的新麂皮皮鞋,請荷蓀代我在拍賣行寄售。這雙鞋子是好友韓素音從英國倫敦托人送給我的。當時後方小型拍賣行林立,家中存有舶來品和較值錢的衣物的人,會拿去寄售,得款用以貼補日常開銷。荷蓀先是不肯,後來被我說服,但她再三說我定價太低。我說能賣出就算不錯了。幾天後,她興奮地跑來告訴我,鞋子一寄售就賣掉了,並強調當初她就說價錢訂得太低,提高些就好了。把售款交給我後,嚷著要我請客,到華西壩「 TipTop」咖啡店喝下午茶。6月我畢業之際,荷蓀買了三件同花色的綢料做成旗袍,分送給我和賦蕭,一件留給她自己。我穿著這件旗袍照了戴方帽子的畢業照。參加畢業典禮時,荷蓀叫我到她鞋櫃找一雙合意的鞋子,我打開鞋櫃時,我那雙灰藍麂皮鞋赫然在其中。她說:「不要生氣,我知道你喜歡這雙鞋,就算是我送你的畢業禮物吧!」她的用心怎能不深深感動我!
這時,荷蓀和賦蕭還不放棄,又忙著為我介紹男朋友。荷蓀請何遠經邀請一位單身工程師,賦蕭邀了兩位年輕未婚的醫師到荷蓀家吃晚飯。結果他們無意,我也無心,「相親」一幕無疾而終。最後荷蓀諄諄勸我:「我看來看去還是那位孫小子對你最誠心,你還是回重慶吧。快三十了,還東挑西選,當心沒人娶你。」
峨眉山見佛光倒映
我即將離開成都返回重慶時,燕大校長梅貽寶夫婦邀我同遊峨眉山,我欣然應允。梅校長夫婦、教育系廖泰初教授、一位女士(忘記姓名,是梅家友人)加上我,一行共五人,包租一條帶篷的木船,由船夫帶路,沿岷江向西南悠然划行。沿途數度停船登岸,除欣賞兩岸美麗的自然風光外,還體驗了四川村莊的樸實民風。船行至樂山,改乘公路客車到鄰縣峨眉,抵達目的地峨眉山。在樂山,我們應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在台灣曾任教育部長、國史館館長等要職)的熱誠邀請,停留一日,參觀四川大學及從武昌遷來樂山的武漢大學。
峨眉山海拔三千多公尺,在四川西南的峨眉縣境內,是我國的著名佛教聖地。重疊秀麗的山巒,蓊郁的林木、飛瀑、流泉,神奇的金頂佛光、佛燈,兩百多所大小寺廟,教人流連忘返,連高山上成群的猴子,也為遊客們津津樂道。山下有出租的滑竿(滑竿是兩根粗竹竿中間懸掛著坐椅,由兩個身強體壯的年輕人前後抬著,是年老者或婦孺登山的工具),但我們取步行,一路慢慢地走,隨興觀賞。共走了三天,夜宿寺廟客房,倒也方便自在。遊過報國寺、萬年寺、白龍洞、清音閣、一線天、洪椿坪等名勝後,到了最高也最有名的金頂寺。這裡海拔高,氣壓低,空氣稀薄,六月炎熱天,山上也有如冬季,十分寒冷。我們都從廟中租了棉衣,圍爐烤火取暖。第二天清晨起床,發現每個人的臉部都變了形,臉和手、腳都腫脹了,眼痛頭暈,呼吸急促、困難,山上住持告訴我們是「高山症」,其中最嚴重的是梅貽寶校長,雇了滑竿被抬下山。說也奇怪,到了平地症狀馬上消失了。不過,在金頂,除了梅校長,我們四人未放棄機會,在導遊引領下,下午兩點鐘左右爬到金頂最高處的平臺,俯瞰懸崖下萬丈深谷,看到對面山谷中出現太陽反射出來的大光圈(俗稱佛光),光圈裡映著自己的倒影。這種自然界絕奇之景,一生中難得一見!
有些鄉下來的朝拜者見到這種影像,認為自己「得道」,遂忘我地跳下懸崖,葬身谷底。為此,這裡用粗鐵鍊隔開,並寫有「想一想,跳不得」的告示。傍晚天色將暗時,可以看到千萬盞光閃閃的「佛燈」,在蒼綠的山谷深處飄浮。據說是這一帶山中蘊藏豐富的磷礦所致。回程我們順路還遊覽其他的名勝,如樂山、岷江東岸的世界獨一無二的石刻大佛,名妓薛濤殉情的古井。二十一天峨眉山之旅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梅校長夫婦的關懷和廖教授一路上殷勤的照拂,雖使我無限感激,但我去意已決,不願多生枝節。
我終於讀完第四年大學課程,於1943年(民國32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學畢業。父親當年的叮嚀使我受用終生。持有大學畢業文憑,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我站得住腳,能夠發
揮自己的能力為社會服務。